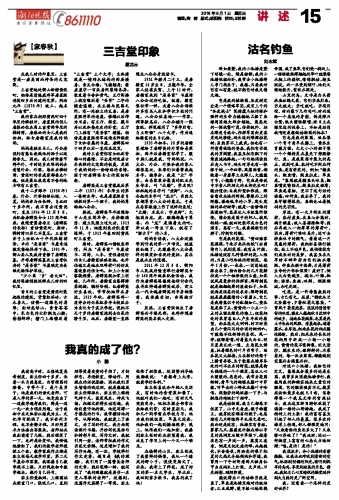易龙云
在我儿时的印象里,三吉堂是一座美丽而神圣的大宅院。
三吉堂地处衡山新桥黄泥町。相传是清振威将军唐星照退役回乡后兴建的宅第,同治九年(1870年)竣工,起名“三吉堂”。
我的家在相距黄泥町四十华里的樟桂冲。唐星照的侄儿唐恭必住在离三吉堂两华里的樟树湾,唐恭必的女儿是我的奶奶,孙女唐翰笙是我的妈妈。
妈妈是独生女儿,外公唐淡轩有意让我做他的孙子以延续香火。因此,我儿时除春节拜年外,平时还多次陪妈妈去看望外公、外婆。每次去樟树湾,黄泥町的亲戚家都要走个遍,但是最让我恋恋不舍的地方唯有三吉堂。
我十二岁那年(1950年)春,外公、外婆相继仙逝;入夏,妈妈亦与世长辞。自此四十多年间,我不曾去过黄泥町。直至1996年12月8日,为纪念唐群英女士125周年诞辰,我随堂舅唐存正(唐群英的长孙)重访黄泥町。斯时,樟树湾旧居已不复见,三吉堂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陆续拆除,幸而“是吾家”书屋奇迹般完整地保存下来。1991年,衡山县人民政府重修了唐群英墓,并将唐群英墓及三吉堂仅存的“是吾家”书屋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少小离‘乡’老大回”,我的思绪悄然沉醉在儿时的回忆里。
昔日的三吉堂是黄泥町最起眼的建筑。背靠红茹岭,古木参天,仿佛一道绿色的屏障;面对龙形山,青青苍苍中,乳白色的云纱飘曳山腰,影影绰绰;槽门上端镌刻着“三吉堂”三个大字;主体建筑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青瓦白墙,飞檐翘角;整座屋宇一百来房间装饰各异,散发着书香和贵气;正厅阁楼上嵌有镶刻着“圣旨”二字的镀金匾额。在主楼与花园之间,有一处独立的瓦房,是唐星照将军的老屋,修缮以后辟为书房,有正厅、课室、藏书库以及私塾先生的卧室;正厅门上挂有“是吾家”横匾,相传是唐星照将军延请名师课教子女和亲属的书屋。唐群英四十四岁以后一直住在这里。
我对三吉堂怀有如此刻苦铭心的感情,不全是对这座古朴典雅的大宅院的钦羡,更源于我妈妈的一份特殊的亲情,源于对唐群英女士的深切怀念。
唐群英是三吉堂落成后第二年(1871年)冬降生的第一条新生命,也是唐星照亲自调教的第一个孩子。我妈妈尊称她八公公。
据说,唐群英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立过大功。1913年11月,她遭到袁世凯悬赏通缉,于1915年春回到黄泥町三吉堂。
斯时,唐群英心情极度郁愤,闷在“是吾家”书屋读书、写诗。入冬,堂侄唐淡轩的女儿唐翰笙呱呱坠地,也许侄媳又是她在双峰荷叶的好友葛健豪的侄女吧,加上小女孩容貌娟秀,唐群英视如掌上明珠。几年间,唐翰笙出落得娇柔妩媚,聪明伶俐,让唐群英好生喜欢,常常把她带在身边。1925年秋,唐群英将一度停办的白果红茶亭女校改办为岳北女子实业学校,便把不足十岁的唐翰笙抱到去白果的轿子里。此后,唐翰笙一直跟随在八公公身边读书。
1931年腊月二十三,是唐翰笙16岁生日。豆蔻年华,全家人设宴庆贺。上午11时许,唐翰笙来到“是吾家”书屋请八公公过府吃饭。饭前,翰笙像往常一样,央着八公公请教许多有关人生和学识方面的问题,八公公欣喜地一一作答。稍事歇息后,八公公铺开一张宣纸,挥笔题写了“多学则智,自立即强”八个大字,作为送给翰笙的生日礼物。
1935年初冬,20岁的唐翰笙嫁给了唐群英的外曾孙易秉初。两年后唐翰笙怀孕了,腹中胎儿就是我。听妈妈说,八太公、外公、外婆和我的家人都很高兴。长辈们忙着帮我起名字,按辈分,我是“业”字辈,由易家辈分最高的纪五先生命名,叫“业麟”,学名呢?奶奶起的名字叫“虎卿”,八太公起的名字叫“龙云”,当然大家都尊重八太公的意见,于是在易家族谱上作了这样的表述:“业麟:名龙云,字虎卿”,大概因为龙、虎、麒麟都属于尊兽,而“龙”是溜着走的吧,所以我一降生下来,就有了“溜古子”的小名。
妈妈告诉我,八太公没能等到听我的第一声啼哭,就溘然仙逝了。无缘感受八太公慈祥的微笑和亲昵的爱抚,实在是我永生的遗憾。
2011年12月8日,衡阳市人民政府隆重举行唐群英女士14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我作为唐群英思想理论研讨会代表再次拜谒唐群英故居。肃立在一代女魂唐群英的半身铜像前,我倍感亲切,亦思绪万千。
显然,三吉堂因诞生了唐群英而平添光彩,也将伴随唐群英的英名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