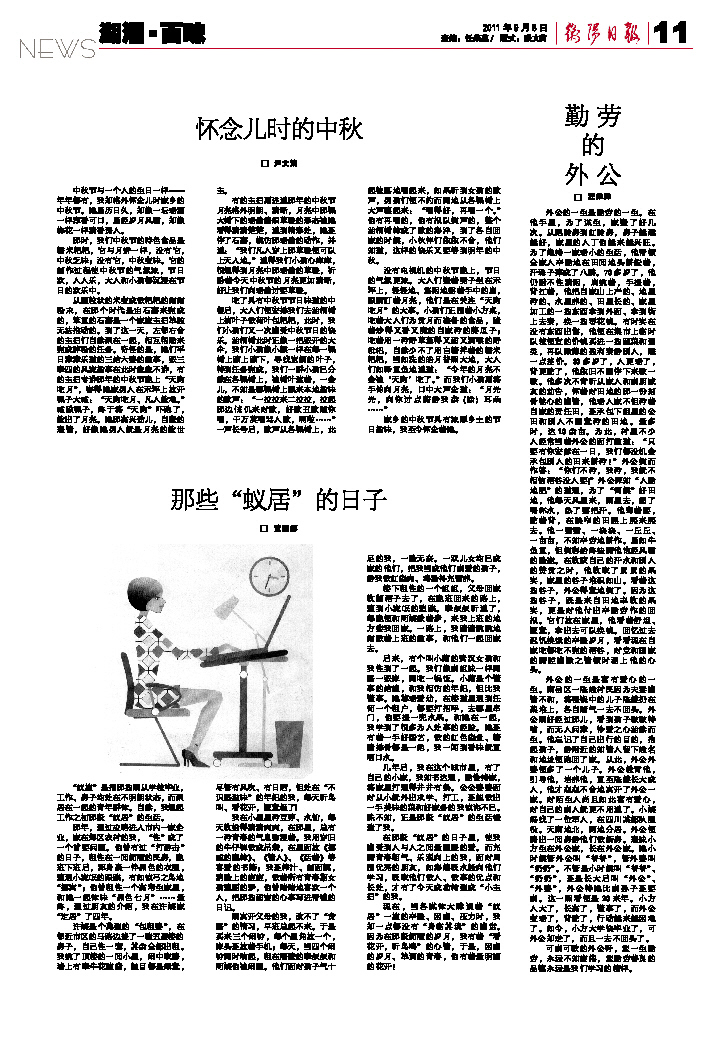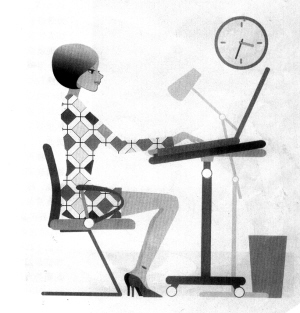“蚁族”是指那些刚从学校毕业,工作、房子均处在不明朗状态,而聚居在一起的青年群体。自然,我想起工作之初那段“蚁居”的生活。
那年,通过应聘进入市内一家企业,家在郊区农村的我,“住”成了一个首要问题。也曾有过“打游击”的日子,租住在一间简陋的民房,晚班下班后,浑身裹一件黑色的衣服,遭遇小流氓的跟踪,有如惊弓之鸟地“挪窝”;也曾租住一个高考生家里,和她一起体味“黑色七月”……最终,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在许姨家“定居”了四年。
许姨是个典型的“包租婆”,在邻近市区的马路边盖了一幢五层楼的房子,自己住一套,其余全部出租。我挑了顶楼的一间小屋,闹中取静,墙上有牵牛花缠绕,触目都是绿意,尽管有风吹、有日晒,但处在“不识愁滋味”的年纪的我,每天听鸟叫、看花开,惬意极了!
我在小屋里种豆芽、水仙,每天收拾得清清爽爽,在那里,总有一种青春的气息弥漫着。我用穿旧的牛仔裤做成吊袋,在里面放《挪威的森林》、《情人》、《活着》等喜爱的书籍;我还榨汁、制面膜,消脸上的痘痘,做着所有青春期女孩瑰丽的梦,也曾暗暗地喜欢一个人,把那些甜蜜的心事写进带锁的日记。
刚离开父母的我,改不了“贪睡”的惰习,早班总起不来。于是买来三个闹钟,每个屋角放一个,床头还放着手机;每天,当四个闹钟同时响起,租在隔壁的李叔叔和阿姨也被闹醒。他们面对孩子气十足的我,一脸无奈。一双儿女均已成家的他们,把我当成他们亲爱的孩子,给我做红烧肉、鸡汤补充营养。
楼下租住的一个姐姐,父母回家收割稻子去了,在晚班回来的路上,遭到小流氓的追踪。李叔叔听说了,每晚便和阿姨散着步,来我上班的地方接我回家。一路上,我蹦蹦跳跳地细数着上班的趣事,和他们一起回家去。
后来,有个叫小菊的武汉女孩和我住到了一起。我们像亲姐妹一样同睡一张床,同吃一锅饭。小菊是个懂事的姑娘,和我相仿的年纪,但比我懂事。她尊老爱幼,在楼道里遇到任何一个租户,都要打招呼,去哪里串门,也要提一兜水果。和她在一起,我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经验。她还有着一手好厨艺,做的红色烧鱼、糖醋排骨都是一绝,我一闻到香味就直咽口水。
几年后,我在这个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小家,我知书达理,勤俭持家,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公公婆婆面对从小就外出求学、打工,还能做出一手美味的菜和好家务的我惊诧不已。殊不知,正是那段“蚁居”的生活锻造了我。
在那段“蚁居”的日子里,使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爱。而充满青春朝气、乐观向上的我,面对周围优秀的朋友,如海绵吸水般向他们学习,吸取他们做人、做事的优点和长处,才有了今天成功转型成“小主妇”的我。
现在,当各媒体大肆谈着“蚁居”一族的辛酸、困惑、压力时,我却一点都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在那段简陋的岁月,我有着“看花开,听鸟鸣”的心情,于是,困惑的岁月、单调的青春,也有着最明媚的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