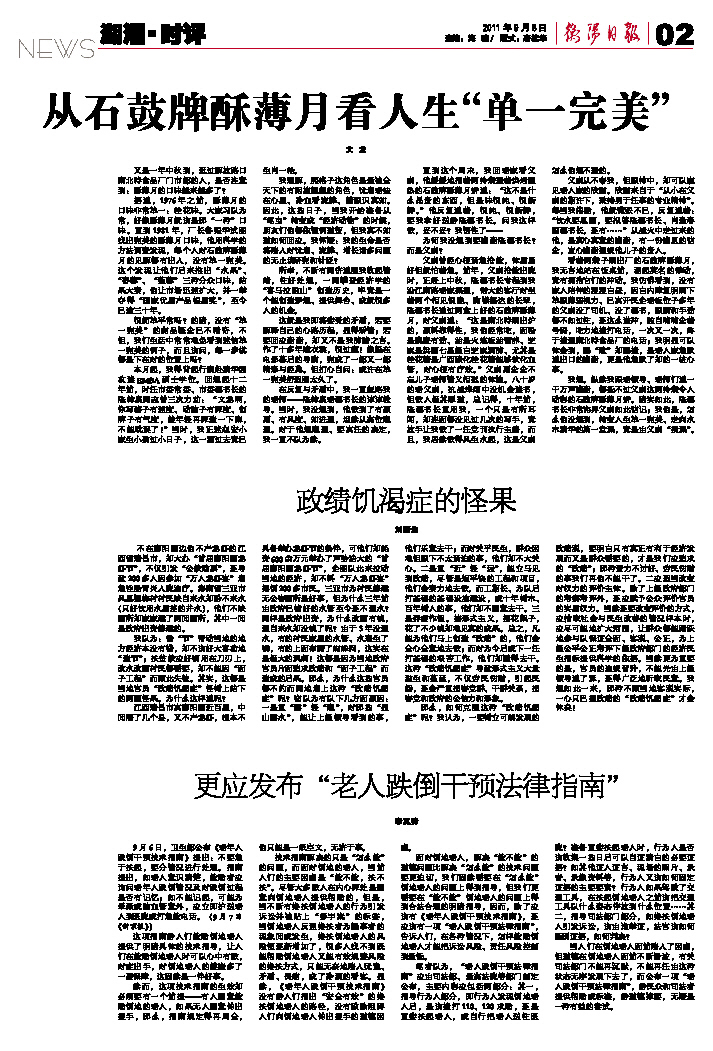9月6日,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指南提出,如老人意识清楚,救助者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护送老人到医院或打急救电话。(9月7日《新京报》)
这项指南给人们救助倒地老人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技术指导,让人们在救助倒地老人时可以心中有数,对症出手,对倒地老人的健康多了一层保障,这固然是一件好事。
然而,这项技术指南的生效却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有人愿意救助倒地的老人,如果无人愿意伸出援手,那么,指南规定得再周全,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无济于事。
技术指南解决的只是“怎么救”的问题,而面对倒地的老人,当前人们的主要困惑是“救不救,扶不扶”。尽管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是愿意向倒地老人提供帮助的,但是,当不断有搀扶倒地老人的行为引发诉讼并被贴上“彭宇案”的标签,当倒地老人反诬搀扶者为肇事者的现象间或发生,搀扶倒地老人的风险便逐渐增加了,很多人找不到既能帮助倒地老人又能有效规避风险的搀扶方式,只能无奈地陷入犹豫、矛盾、畏缩,成了冷漠的看客。显然,《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没有给人们指出“安全有效”的搀扶倒地老人的路径,没有破除阻碍人们向倒地老人伸出援手的道德困惑。
面对倒地老人,解决“救不救”的道德问题比解决“怎么救”的技术问题要更迫切,我们固然需要在“怎么救”倒地老人的问题上得到指导,但我们更需要在“救不救”倒地老人的问题上得到合法合理的明确指导,因而,除了应该有《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还应该有一项“老人跌倒干预法律指南”,告诉人们,在各种情况下,怎样救助倒地老人才能把诉讼风险、责任风险控制到最低。
笔者以为,“老人跌倒干预法律指南”应由司法部、最高法院等部门制定公布,主要内容应包括两部分:其一,指导行为人部分,即行为人发现倒地老人后,是该拨打110、120求助,还是直接扶起老人,或自行把老人送往医院?准备直接扶起老人时,行为人是否该收集一些日后可以自证清白的必要证据?如其他证人证言、现场的照片、录音、录像资料等,行为人又该如何固定证据的主要要素?行为人如果驾驶了交通工具,在扶起倒地老人之前该把交通工具以什么姿态停放到什么位置……其二,指导司法部门部分,如搀扶倒地老人引发诉讼,该由谁举证,法官该如何甄别证据,如何判决?
当人们在倒地老人面前陷入了困惑,但道德在倒地老人面前不断滑坡,有关司法部门不能再沉默,不能再任由这种状态无序发展下去了,而公布一项“老人跌倒干预法律指南”,给民众和司法者提供帮助或标准,给道德撑腰,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