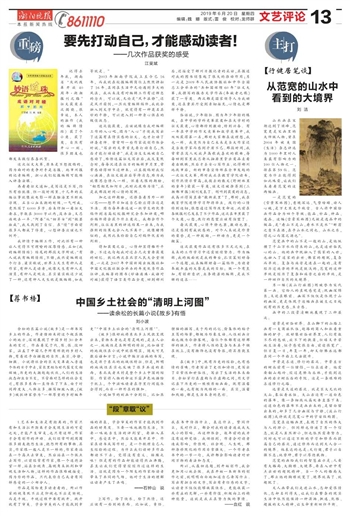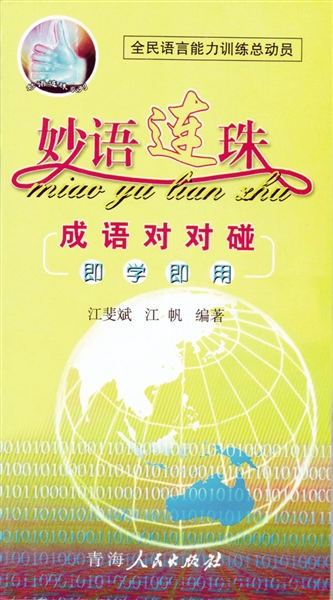记得去年底,湖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湖湘报刊之路”征文获奖名次揭晓,很幸运,本人的拙作《我的编辑情结》获了个小奖。获了奖,自然有开心一刻,很多朋友也都发来微信恭喜祝贺。
这次征文大赛,原本是不想投稿的,因为面对的竞争对手是省报、地市州报的记者编辑,担心我们校报编辑可能难入评委法眼。
再看看征文通知,是写还是不写,仍然有些犹豫。但一段时间里,十几年的采编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不断地浮现。正当心血来潮的时候,一气呵成,竟然写了6000多字。后来仔细一看征文要求,字数在3000字以内,没办法,又忍痛砍去一半。“阿婆”从“初笄女”到“梳罢妆成”,我又找到了自信。在“情”字面前很多人都成了俘虏,心想评委应该也不例外。
我钟情于编辑工作,对此怀有一种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深厚情感。正如《我的编辑情结》结尾的那段文字所说:“有人说我有编辑情结,不错,我热爱编辑这个行当。梁实秋说,世界上天生有种人是作家,有种人是读者,就像天生有种人是演员,有种人是观众。其实梁实秋还少说了一种,还有种人天生就是做编辑,如我等就是。”
2003年湘南学院成立至今已16年,而我就在校报编辑岗位上默默耕耘了16年。其间在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我从来没有对编辑工作有过懈怠的念头。可以说,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风刀霜剑,一旦伏案编辑稿件,我就会融入到文字中去,就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平静,可以进入到一种身心俱在的极佳状态。
这次能获奖,应该说缘自我对编辑工作的入心吧,因为“入心”才使我写出了这篇有真情实感的征文,也才打动了评委老师。常常听一些作家谈创作体会时说,“写出的文章首先要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读者”。我是活生生地被自己感动了,难怪这篇征文写出后,我反复默念时,每每沉浸在往日的编辑岁月里,常常感动得回不过神来,以至投稿时我信心满满。在征文投出后等待消息,难为我就像思念情人一样,怀着无限的期盼,“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正是我那段时间心情的写照。
加之这种期盼,还掺杂着另外一种心思——想早日知道自己验应得准还是不准。因为每年要选送一批学生的优秀稿件到省高校校报研究会参加评奖,哪些稿件将会获个什么奖次,我都会作个判断,往往省里的评选结果一出来,与我推断的结果也会八九不离十。就像赌博似的,我用此来检验自己对稿件优劣的判断。
得知获奖之后,心情却显得格外平静,不过也勾起我对过去几次重要获奖的回忆。犹记两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一次是2007年中国新闻出版报社和中国文化报社联合举办的年度优秀作品征评,我编著的图书《妙语连珠·成语对对碰》获得了语言类作品金奖。回到郴州后,还接受了郴州日报记者的采访,其报道对我的图书销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次是2009年人民政协报社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共和国辉煌60年”征文大赛,我撰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奉献者之歌》获了一等奖。两次都是国家领导人为我颁奖,还在贵宾厅受到亲切接见,心情也是那样平静。
俗话说,少年轻狂。因为年少年轻的缘故,在中学的学科竞赛获奖和在大学时的征文获奖,心情都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一年在中学的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中,我双双获得第一名,那时大家都在谈理想,我也一样,我竟然为自己未来是当大作家还是当数学家而感到矛盾不已。那段时间,我常常在没人处放声高歌我喜欢的歌曲,每每回到家里我总要从抽屉里拿出奖品左看看右瞧瞧,然后才去安心写作业。记得郴州地改市后,新的市委宣传部在全市发起的一次征文大赛,那时我正在教育学院读书,创作热情非常高,我投去的散文《野树林里的童年》荣获一等奖,该文还被推荐到《三湘都市报》副刊发表了。刚听到获奖的消息,我高兴得简直要“歇斯底里”了,那时,我在教育学院进修学习即将毕业,改行的心情特别迫切,很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此前在各级报刊已发表了不少作品,这次在市里获了个大奖,心想,改行的愿望应该有指望了。
每次获奖,心情平静也罢,激动也罢,还是感到有成就感的,对个人来说是珍贵的荣誉,是一种鼓励,一种动力,更是一个鞭策。
这次获奖作品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未来的工作学习中还需继续努力。作为编辑,我的版面就是我的舞台,扎实策划好每一个选题,认真编辑好每一篇稿件,为读者奉献丰盛的大餐是我的目标;做一个有良知、有创新意识、业务精湛的编辑,是我不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