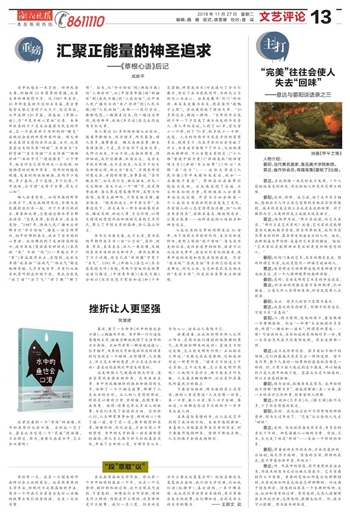老早就想出一本言论、时评或杂文集,但翻阅33本厚厚的剪报,此类文章的确写得不多。从1987年至今,30年所发表的不过四五百篇,有分量能登大雅之堂的少之又少。经过筛选,从中选择120多篇,拼凑成《草根心语》,乃“平民百姓心里话”之意。本书所收录的不少是关注基层与民生的作品,是一个农家弟子用仰视的“眼光”窥视社会后的所思所感所悟,绝大部分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当然,也有芸芸众生的无畏“呐喊”。全书分为“乡村寄语”“直言快语”“点击传媒”“湖湘时评”“品味学习”“理论探索”六个章节,权当对自己写作的又一次检阅。回想构思时的艰辛孕育、写作时的尴尬境遇、发表时的痛快淋漓,其间多少感慨,多少喜悦,多少遗憾,多少忧思,个中滋味,正可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鄙人出身贫寒,如同卑微的野草扎根乡下,离大地贴得很近,长期与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对于乡亲们的诉求、希冀和抗争,总想通过媒体寻求解决途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1987年,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新辟专栏“今日论坛”,播发一些言辞犀利、切中时弊的杂文,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我仿佛找到了发泄情感的窗口,连续写成《莫误农家好时光》《农药姓“农”不姓“钱”》《一年能生多少“蛋”》等篇投寄出去,没想到,这些文章因“说真话”“接地气”“扬正气”颇受编辑青睐,几乎百发百中。乡亲们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些稿子后,夸我为农民“说了话”“出了气”“撑了腰”“解了难”。后来,从“今日论坛”到《湖南日报》的“三湘时评”,从《中国青年报》的“新语丝”到《农民日报》的“三农论坛”,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央广时评”到《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我都一一进行尝试,颤颤悠悠,一路摸索过来,均一路过关斩将,连续命中,就连《半月谈》杂志也约我写专栏文章。
本人有过30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随着年龄增大,经历增多,所见甚杂,阅人更多,遇事愈杂。眼见杂物杂事,顿生杂情杂思,于是,忍不住写下这些文字,或即兴而发,不吐不快;或抽丝剥茧,慢评细说;或引经据典,弘扬正义。这些文字既非新闻,也不是论文,而是介于论文与新闻之间,称之为“杂文”。实因其所写对象之杂,并因时借势,杂事杂说。“杂然赋流形”,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并无一定之规矩。杂文只认一个“理”字,就是因事说理。杂文界没有装模作样,没有浅吟低唱,没有无病呻吟,只有真枪实弹,激浊扬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鲁迅笔下,杂文成为一种自由地摹写世俗、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善的艺术形式,攀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令人高山仰止。
本书定为杂文集,也不太准,因为我的早期作品多为一些“小言论”,简朴、坦荡、率真,直来直去,让人一看就懂,反映的是老百姓的诉求和呼声,居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使自己在“新闻圈”中有了“名气”。1991年,《年轻人》杂志以《乐为农民鼓与呼》为题,用两个整版对我的事迹进行报道,《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分别以《欢乐忧愁只有你知道》和《十年笔墨勤,终有成功日》对我进行了全方位展示,坚定了我为农民写作、为时代立言的信心与决心。后来发展为“热门”的时评,再后来发展为杂文,现在居然“赶鸭子上架”,尝试着写起了理论文章。“3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一下子变成了满头白发的半百老人。有人开玩笑说,人到了60岁,官大官小一个样;到了70岁,钱多钱少一个样。我想,人生的价值并不是在乎你的官有多大,钱有多少,而在乎你对社会贡献了什么,为普通百姓留下了什么,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可以告慰大家的是,《“小人物”塑造中国力量》《“新闻危机”搅动官场生态》《讲好“本土故事”》《何必“衣锦”再“还乡”》……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发表后,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有的在社会各界引起较大反响,让我感受到了真诚、正义和良知的力量;有的被收入公务员申论笔试试题。尽管当今社会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变化,尽管国人的心态变得有些浮躁,但“人间自有真情在”,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汇聚正能量——始终是我的人性担当和神圣追求。
入选此书的文章时间跨度达30余年,为了保持文章的时代性、真实性和史料性,原则上保持“原汁原味”。杂文是历史的记录,是社会进步的缩影,读者可以从这些文章中,感受时代变化的速度、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农民真情的温度。尽管“农业税”“农民负担”等名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与土地、生态和农民息息相关的“美丽乡村”,仍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