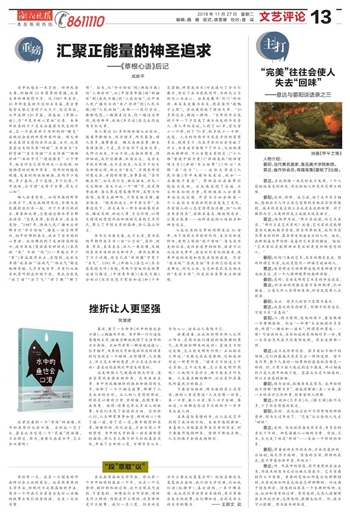人物介绍:
晏阳,当代著名画家,鲁迅美术学院教授。
意达,省作协会员,有随笔集《爱极了》出版。
意达:当我拍摄一朵花时我才发现,一个人想把他感受到的美,传达给他人时竟然是那么的难。
晏阳:是的,很难。我总说,端了大半辈子相机,想拍出点儿什么自己需要的东西其实很难做到。技术既是表达的工具也是表达的保障。对于摄影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就是语言。
意达:难怪罗丹说:“照片在说谎,而艺术真实。”那什么是艺术家呢?我想,艺术家就是能够禀承天赋和勤学苦练,将自然界的美,或利用自然界美的材料、器具将美传递出去的人吧。由此,我特别喜欢罗伯特·麦基对艺术家的描述,他说:“艺术家就是能够讲出更深刻更美妙的感觉的人。”
晏阳:任何门类的艺术,其目的都是表达。因而所谓艺术家,也就是能用一种语言说话的人。
意达:能否将这句话理解成能用某种语言自由地表达,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的巅峰体验。
晏阳:是的。自由是所有艺术家的毕生追求。
意达:但自由的前提是遵守某种规律,比如勤奋。上苍允许人获得好东西,但首先需要人去刻苦。
晏阳:未必。很多人刻苦只是因为喜欢。
意达:我喜欢的东西好多。但都不刻苦追求。可能不是“真喜欢”。
晏阳:人,精力有限,能做的很少,甚至做好一件事都很难。但这“一件事”又关联到许多东西,所谓“一桶水和一滴水”,所谓厚积薄发……难!可话说回来,当你知道的东西相对多一些,有一天你会忽然在不经意间发现,原来道理都一样。
意达:这点我特有同感。很多看似不相干的领域,它们的最高点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整个自然界,整个人类的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都是一样的。但,只有少数人能达到这个高度。所以相通的只是人类中的极少数。芸芸众生是不相通的,所以才会感到孤独。
晏阳:换句话说,孤独原本是常态。我年轻时就不理解“理解万岁”。谁能理解谁?某一方面、某一点的共识已然珍贵,别奢望别人理解。
意达:你说和《兰亭序》比,《滕王阁》技巧太多,少了些真情感的表达。
晏阳:是的。我也说过我听不得整场的斯特劳斯,因为太过华丽了。“完美”往往会使人失去“回味”。
意达:是的。你还说你喜欢贝多芬,贝多芬的音乐少华丽,却充满撼人心魄的力量。你说,艺术,太完美了就是“封闭”——自成一个封闭的体系。
晏阳:带着些许天然的东西,才会是最好的。应该说,越天然才越好。情感的宣泄、精神的表达,能不带着些许率意、率性么?
意达:嗯。作品中的情感,创作者有就会溢出来,用技术刻意为之往往缺乏感染力。艺术家看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表达他理解到的,或者说他如何表达他是怎样理解的。而这属于情感部分。情感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吸呐、关注、认识和思考的过程。有情感的,无需人提醒便会自然地宣泄;无情感的,提醒也枉然。但,技术可以提醒。因为技术好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