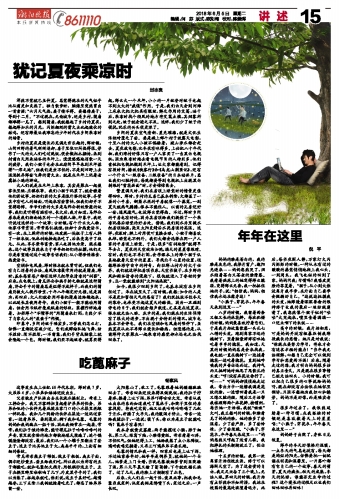浑然不觉就已至仲夏,总觉得现在的天气似乎比从前更加炎热了。独自散步时,脑海里突然冒出一首童谣:“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要想借扇子,等到十二月。”不过现在,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蒲扇都难得一见了。想到蒲扇,我就想起了乡村的夏夜,想起那如水的月光,闪烁翩跹的萤火虫此起彼伏的蛙鸣,还有那最让我难忘的少年时代在乡间乘凉时的场景。
乡村的夏夜是漫长而充满无穷乐趣的。那时候,山间田野的暑气刚刚退却,房子里依旧闷热得很。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们吃过晚饭,便会搬把木躺椅,来到村前白天用来晒谷的禾坪上,慢慢悠悠地消散一天的疲劳。我们小孩子也会在此期间早早来到禾坪谋得“一席之地”。但我们是坐不住的,不是到田野上去追逐捉弄那些飞舞的萤火虫,就是在禾坪上玩着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大人们说是在禾坪上乘凉,其实是聚在一起谈家长里短、庄稼农事。我们小孩子玩累了,就会缠着他们讲故事。奶奶们讲的大多是狼外婆的故事,尽管其中有吃人的场面,听起来有些害怕,但我们却并不觉得恐怖。爷爷们讲的大多是马师公斩妖除魔的故事,我们更听得有滋有味。长大后,我才知道,马师公原来是我们湘南地区的一个道教人物。印象中,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什么大人物,他家非常贫困,常常忍饥挨饿,但却十分热爱读书。有一次,在上厕所的时候,他发现一块板子上有人掉了一粒米饭,他麻利地捡起来吃了,后来竟高中了状元。从此,享尽荣华富贵,家人也因他为荣。现在想来,这个故事显然来自于爷爷奶奶们的杜撰,他们无非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从小得珍惜粮食、热爱读书。
空调和电风扇,那时根本就未曾听说,但我们也有自己消暑的办法。扇风取凉最常用的就是蒲扇。那时,基本每家每户都有这样几把带来清凉的“利器”。后来,在电视上,看见济公和尚手持之物就是这种蒲扇。济公手中的蒲扇总是烂得不成样子,而我们的蒲扇则被大人视作珍宝,十年八年都完好无损。这是因为,买回后,大人们就会用布条把蒲扇边给缝起来,以此延长其使用寿命。我们小孩子一般不能动用蒲扇,但会用书纸折叠成纸扇的形状,装模作样地扇着。如若那个“不懂事的”用蒲扇来打闹,自然少不了自家大人的“栗凿子”伺候。
印象中,乡间的蚊子确实多,不管我们怎么打,仿佛一直都没有减少过。它们成群结队地飞舞,防不胜防、烦不胜烦,一不留意,我们手背或脑袋上就会隆起一个包。那时候,我们买不起蚊香,就算买得起,那么大一个禾坪,小小的一片蚊香对蚊子也起不到太大的“威慑”作用。于是,我们白天会到河滩上采来大把大把具有驱蚊、解乏作用的艾蒿,晒干后,乘凉时找个顺风的地方将艾蒿点燃,其烟雾所到之处,蚊子就会避之不及。这样,我们少了蚊子的侵扰,玩乐的兴头便更浓了。
乡间的夏夜空气清新、星光璀璨,就是文化生活相对匮乏了些。要是碰上哪个村子放露天电影,十里八村的大人小孩不惧酷暑,跋山涉水都会赶去。夏夜放电影,比冬夜有味得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湾村好像只有一户人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因为乘凉时跑去看电视节目的人特别多,他们索性把电视机搬到禾坪上,让大家都能看到。记得有段时间,播放《侠客行》和《乌龙山剿匪记》,还有一个什么“一级准备、二级准备”的日本动画片,总让我们心驰神往,每晚都要等到电视机上出现黑白刺眼的“雪花画面”时,才会悻悻离去。
繁星满天时,我们在房顶上睡觉时的情景更值得回味。那时,乡村的瓦房已基本拆除,大都盖了一层的小平房。钢筋水泥的平房就像一个蒸笼,一到夏天就热气腾腾,根本不能住人。以前的瓦房还好一些,通风透气,也没那么觉得热。不过,那时乡间的平房也有好处,因为其房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乘凉玩耍后睡觉的好去处。傍晚,我们到水井里提水把房顶淋湿,浇灭太阳炙烤后水泥房顶的高温。这样,夜深时,摊上竹席便可直接去睡。小孩子都喜欢扎堆,睡觉也不例外。我们大都会选择在同一户人家的平房顶上睡觉。于是,很多“有利地势”就得早早去占。夏夜的天空皎洁如洗,满天的星星像眼睛。有时,我们也不再打闹,会学课本上的那个孩子认真地数着天空中的星星,寻找北斗七星的位置,遐想那浩渺宇宙中的神奇,向往那山村外的大千世界。我们就这样把房顶当床,天空当被子,在乡野的风和稻谷清香的浸染下,很快就进入了香甜的梦乡,且一觉就能睡到“太阳晒屁股”。
如今,我很少回到乡间了,也基本没有在乡间住过了。呆在城里久了,有时候,我想:如今的人是不是更加害怕天气的恶劣了?我们既抵抗不住冬天的寒冷,也承受不起这夏天的酷热。因为一旦碰到停电的日子,我们就会怨声载道,尤其是在这夏夜,根本就无法入睡。庆幸的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保障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出现十分特别的情况,城市也基本不会停电。我们在空调和电风扇的陪伴下,虽然夏夜从此不再那么漫长和酷热,但遗憾的是,从前那种大家聚在一起乘凉的感觉却永远也无法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