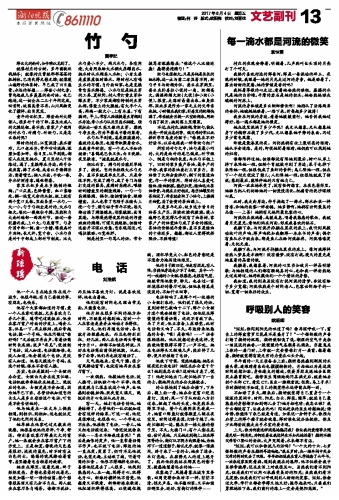那么大的南竹,如今难以见到了。
就像村庄的古树,多年前被砍伐殆尽;就像村庄曾经郁郁苍苍的枞树林,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早已成了旧日盛景,永远的怀想……那些小村之旁,曾勾起我几多羡慕的南竹林,也已绝迹。这一切全在二三十年间完成。回首间,故园美景不再,山川风物变化了模样,面目荒芜。
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南竹大得惊人。很多竹干的下部,甚至比成人的大腿还粗。要不然,家家户户使用的竹水勺、竹潲勺、竹淤勺,又是怎么来的呢?
那时的村庄,江宽流清,泉水密布。几口老石井,常年咕咕流淌,深碧如墨如眸。每日里,从早到晚,都有人在这里挑水。夏日里村人干活路过,渴了,直接蹲在井边,两手合成浅窝,捧了水喝。或者以手俯撑井沿,努着嘴巴,插入水面,牛饮一番。井水甘冽清凉,通体舒泰。
家里水缸多是本乡烧制的粗陶,广口仄底,色泽酱紫。缸口靠墙处,搁一块宽尺余的木板,板上放有两个宽口瓦钵,里面各置一水勺,一大一小,勺子勺柄全是竹的。大水勺粗大,堪比一截粗壮牛腿,显然取自大南竹端部一两段竹节,经过一番削磨而成,上口大,勺底留节。勺身外围中部一侧,凿一方槽,镶嵌扁竹片为柄,长尺许,宽寸余。小水勺当是竹干中部或上部竹节制成,比大水勺要小不少。两只水勺,各有用途。大者用来给大水锅大鼎罐舀水,挑水时从水桶舀入水缸;小者主要是煮菜煮饭时添水,那时村人有喝生水的习惯,自外面回家,也是直接拿它舀水解渴。小水勺还是淋豆芽的工具。夏秋间,村人常打黄豆芽和绿豆芽。不少家庭都有特制的豆芽木桶,像竖立的大腰鼓,有大半个人高,两端一般大小,上有木盖,下有漏洞。早上,常有人陆续提着豆芽桶到水井边,拿小水勺从井里舀水淋透。顺便扯出一些又高又嫩的豆芽,漂洗干净豆壳,作为早餐或中餐的菜肴。
水勺从早到晚,总是湿漉漉的。盛放的瓦钵里,也通常积聚着余水。在我童年时期,有一个无人不知的谜语:“喜鹊尾巴长又长,白日洗澡,夜里歇凉。”谜底就是水勺。
相比而言,潲勺的功能则单纯多了。按说,它的长相跟大水勺无异,差不多就是孪生兄弟。只是命运不同,它成了潲勺,成了专门与猪打交道的器具。煮潲时舀潲水,喂猪时刮槽盆里的剩渣残汤,一勺一勺舀潲添潲。偶尔,猪拱嘴挑食,踩踏槽盆,主人也拿了它顺手在猪头上挖一勺子。潲勺似乎常年不洗,每天都沾满了潲渣糠灰,形容肮脏,面目黑透,与那浸泡得发黑朽边的污渍斑斑的潲桶,可谓天然绝配。但猪对这些并不深以为意,它乐观闲适,吃喝拉撒睡,心宽体胖。
倒是村里一句骂人的话,常令挨骂者深感憋屈:“你这个人比猪还蠢!蠢得要挖潲勺!”
淤勺也很粗大,只是其柄是长长的细木棒,这一点与前二者显著不同。淤勺平日与淤桶为伍,要么在茅厕里,要么在卧房拉小便的一角。淤桶高大,满满两桶大淤(大便)和小淤(小便),很重,走路时易荡出来,浊臭浓郁,因此多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母亲来挑。小时候在我们家,卧房里的淤桶快满了,母亲就会另提一只空淤桶来,用淤勺舀了驳开,挑到园土里灌菜。
不过,在村庄,挑淤桶,拿淤勺,被认为是一件没出息的事。做父母的常以此教训学习马虎的孩子:“你现在不好好读书,以后也跟我一样拿淤勺把!”
所有的竹勺之中,油勺是最小巧的,大约是南竹的尾巴做成,竹节短小。倒是勺柄的长度,与水勺不相上下。旧时的家乡盛产茶油,最丰产的年份,我家的茶油要打三百多斤。茶油除了大部分卖掉外,剩下的装进油瓮,作一年的家用。那时村人喜爱吃猪油,猪油肥腻,能疗肚荒,猪油远比茶油珍贵,与现在正好相反。每当油罐里的茶油没了,母亲就会取了小油勺,上楼揭开油瓮,舀了金黄的茶油满上。
只是多年之后,故乡这方昔日的油茶主产区,因滥砍滥伐滥烧,漫山遍野已荒芜得几乎没有了油茶树。家家户户的油瓮油勺成了多余的摆设。茶油的价格连年看涨,差不多是猪油的十倍还多。想想,都让人觉得恍若隔世,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