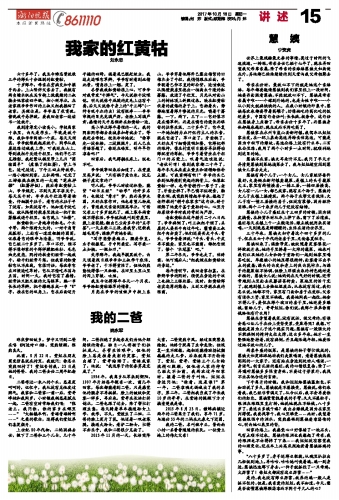六十多年了,我至今难忘曾放牧三年的那头十分温驯的红黄牯。
十岁那年,母亲在贫病交加中撒手西去,上山陪伴父亲去了。我被有两台缝衣机在关市街上做裁缝的二叔接去他家读四年级。初小刚毕业,在老家跟爷爷作田的三叔又把我接回了老家,其理由是,爷爷患了夜盲症,傍晚放牛易摔跤,要我回老家一边读书一边放牛。
我到清潭完小读高小,学校离家十来里。白天是学生,早晚是放牛郎。我和爷爷同睡一个床,每天天刚亮,爷爷就催我起床放牛,同学从我屋边路过喊我上学,可我还在山上。等到我把牛关进牛栏里,他们早已不见踪影。我赶紧从锅里带上几只“圆猪圆羊”(煮熟了的红薯),背上书包,边吃边追。下午三四点钟放学,一路小跑回到家,三扒两咽,吃完了三婶娘热在锅里的一大碗“芝麻拌糖”(红薯拌饭),然后牵红黄牯上山。爷爷规定,不到天黑不准关牛。每天关牛时,爷爷在牛栏边等着检查,仔细摸牛肚子,看它的水肚子平了没有,如果没有平,他知道牛没吃饱,就从隔壁的柴房里抱出一把干红薯藤放进牛栏里,让它晚上“加餐”。
红黄牯长一身纯净的红毛,个头中等,两个眼睛大大的,一对牛角弯成弧形,上面有一道道粗糙的圆圈,记录着它的艰辛与沧桑。听爷爷说,它已经二十多岁了,草口不好。怪不得不像邻家的牛那样膘肥体壮、毛色油光发亮。同村的牧童们经常一起放牛,牯牛们经常斗架,但我家的红黄牯它从不应战。它很听话,每次牵它在田埂边吃草时,它从不偷吃禾苗与豆苗。时间一久,我对它有了感情,经常扯又肥又嫩的大马根草,编一串长长的草辫,把牛缰绳系成一串“8”字,挂在它的双角上,它在后面迈开平稳的四蹄,摇着尾巴驱赶蚊虫,我边走边喂它草辫。爷爷有时看到此情此景,嘴角往上一翘,笑了。
尽管我放红黄牯很上心,可爷爷对我常发“牛脾气”。今天说你牛没喂饱,明天说你牛屁股的皮毛上沾有牛粪,后天又说你牛身上的“牛三蜱”(一种专吸牛血的虫)没有捉净……爷爷审视的目光充满严厉,老脸上写满严肃,感情的天平总倾斜在红黄牯一边。
高小毕业那年暑假的一天,我的同班同学都去县城参加考试去了,等我赶去母校,校长冷冷地说:“你事先一没体检,二没照照片,别人已在考场答题了,你还在咯里。明年早作准备吧!”
回家后,我气得躺在床上,饭也不吃。
爷爷做事回来后知道了,在堂屋里高声说:“只有锅子煮白米,没见锅子煮文章的!”
听人说,爷爷儿时读过私塾,能背“四书五经”“幼学”的许多名句,也做过“秀才”梦,然而美梦未圆,只好在家作田。他也希望儿孙成才,曾送我父亲读到国高毕业,可惜父亲三十多岁就死了。碰上寒冬雨雪做不得农活,爷爷就把我叫到堂屋里,戴上老花镜,翻出已尘封多年的“五字鉴”,一天点教二三段,要我背,还教我练毛笔字,满脸严肃地告诫:
“写字姿势要端正,腰要伸直,右手轻握笔,手中间要空,写字要一点如桃,一撇如刀。”
失学那年,我起早摸黑放牛,白天顶着烈日跟爷爷和三叔学干农活。爷爷老了,干不得重活了,但他仍然勤快得像一只蜘蛛,在田里土里山里的网上穿梭、吐丝。
我至今记得那年冬天一个月夜,爷爷给红黄牯添草的情景。
月亮在爷爷的咳嗽声中爬上东山,爷爷穿着他那件已露出棉絮的旧棉衣去了牛栏,我悄悄跟在后面,爷爷驼着已伸不直的虾公背,边咳嗽边从隔壁柴房里抱出一捆尚未干透的红薯藤,放进了牛栏里。月光从对面山上的树林顶上斜照过来,映在红黄牯伏着的疲倦的身子上,它抬着头,静静地望着那片惨淡的月光,嚼着干薯藤。一下,两下,三下……它好像不是在嚼草料,而是在嚼它的漫长而艰苦的拉犁生涯。二十多年了,它年复一年地把精力血汗化作主人的衣食,现在它老了,草口老了,牙齿钝了,只好在月下细嚼慢咽加餐。它那忧郁的眼神,像在忖度明日能否再拉得动那沉重的犁耙。爷爷弓着背坐在牛栏门口的石凳上,叹着气边咳边说:“老伙计呀!你到我家都二十年了,每年冬天本应煮点黄豆和酒糟给你补点膘,可我家哪有啊!”爷爷的头已垂到他那瘦削突起的胸骨上,他像红黄牯一样,也辛苦耕作一辈子了,老了,牙齿全掉了,早已嚼不烂硬食。触景生悯,我突然同情起爷爷来,想起了老师教的“耕牛农家宝”这句话,终于理解了他爱牛甚于爱孙的心,心里开始原谅爷爷对我的苛刻与严厉。
老红黄牯在这年腊月二十八日死了,爷爷病倒了,叫三叔把牛埋了,共屋的人要买牛肉过年吃,霸蛮要三叔把牛肉分卖了,他们还要买走牛头、骨头。爷爷含着泪说:“牛头、骨头、牛皮再不能卖,家里也不能留,都把它埋了,修个‘衣冠墓’吧。”
第二年冬天,爷爷也走了。临终前,他叮嘱后人:“把我埋在红黄牯坟的旁边。”
每年清明节,我回老家扫墓,在祭拜爷爷的同时,顺便在旁边的牛坟上也插上三根坟签,这时,红黄牯那老实忠厚的憨态,立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