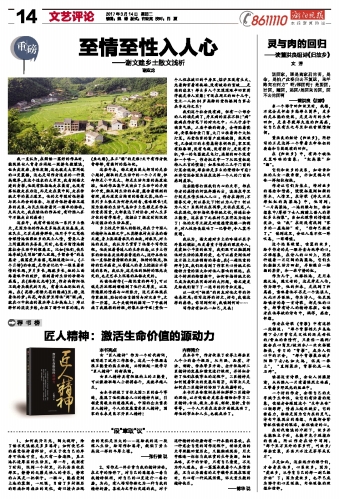文 芳
说回家,那是离家后的苦,是命,是怕/“此春出去不复返,来年路向在何方”呀/那回呢?是要回,讨回,赚回,逃回/是回来的回,回不去的回啊
——董洪良《归家》
当一个游子回归故里时,我想,不完全是怀念乡愁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本能的使然,是灵与肉的生命回归,是要寻获那久违的归属感,让自己在有生之年里和往昔深情相拥。
董洪良的组诗《归故乡》,所抒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带着生命体征的姿态和自然返璞的回归。
在《归故乡》中,有两个被他反复吟咏的意象:“红高梁”和“酒”。
它们和故乡的关系,如母亲和她的儿女一般亲密,亦如灵魂与肉体一样相扶相依。
作者以它们为焦点,将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慢慢拓展到细微的草木、人情里。在诗歌《许久不见那红红的高粱地》中,他写到:“一片高粱地,一地的绿与红,恰如想象中/薄衫下女人胸脯上诱人的晕红多么相像”。当如此深挚的情愫迸发后,让“我”在还没有找到“家乡的一座地标”时,“你却已经老了。” 读到这里,会让人忍不住一阵叹息,一阵唏嘘。
这个远离欲望、喧嚣的故乡,给予作者的是一颗朴素与纯净的心。不难想象,在诗人的心田上,同样种植着一片辽阔的高梁地,它们生机勃勃又活力四射,并酝酿出一缕酒的芬芳,和一抹宁静的红。
作为儿子,双膝拄地,是用来跪天地,跪父母的,这是孝是人伦。作为游子,他的归来,是找到了归属感,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流浪儿,从此不再孤独。作为诗人,他呈现给读者的每一首诗歌,都是他的心音,都带有诗人的精神容颜。让读者在他奉献的诗句中,徜徉,感念,怀想。
作者在诗歌《背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那个背影悄无声息地蹲下去/不管它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骨血的亲情啊,只要你一跪拜/就会在心窝里/被泪水/一次次捂暖捂热。昔日的“背影”,成为人们心中的不舍,“那个背影最后被夕阳降下去/也如大地,化成一捧土”,“直到最后,背影化成一块石碑”。
读罢这首诗歌,会让人泪腺崩溃,从而陷入一片有着强烈立体感,又带着乡野风光的版画中。
一个好的作者,会将自己的文字赋予生命性,让它们有活着的迹象,使读者会跟随这个“生命本体”心潮澎湃,情感上起伏跌宕。它的诱惑力,恰恰是因为它内在的灵气。诗句中展现出的思想、内蕴都会紧紧抓住读者的眼球,抓住读者的心。
在时代潮流的冲刷下,故乡并未能独立于世,未能幸免于碰撞后的伤痛。所以作者在诗中写到:“那千里万里外的家乡啊,叫故乡/那些空巢,其实只不过是茅草或瓦片”。
正是如此,这些远方的游子们,才会身在他乡,心系故乡。因为,“爱故乡,从孕育自己的那一刻已经开始”了;因为爱故乡,也早已成为游子们心灵皈依、肉体皈依的理想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