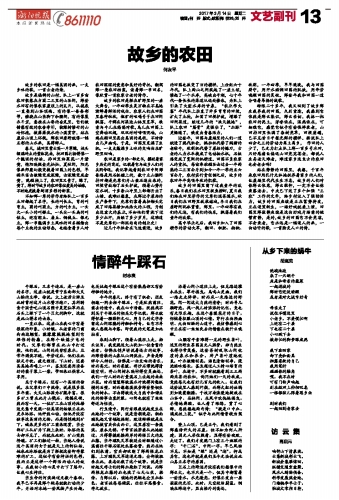故乡的农田是一幅美丽的画, 一支乡味的歌, 一首古老的诗。
故乡是偏僻的山村。队上一百多亩农田散落在方圆二三里的山谷间, 那些水田有的像农家屋顶上的瓦片, 从垅底一直叠到山谷顶端。有的像一条条彩带, 缠绕在山峦脚下和腰间。有的像蓑衣斗笠, 悬挂在山脊的旮旯里。它们被错落有致的农舍牵引, 被绿树修竹的山岭怀抱, 被潺潺流水的小溪贯穿。站在屋后山顶上环视, 那农田原野就像一幅五彩的山水画, 美得醉人。
春天, 垅田里紫云英一片翠绿, 枝头缀满碎点的紫红花朵, 把田园打扮得像一个靓丽的村姑。排田里油菜花一片澄黄, 艳阳映照金光灿灿。夏秋间, 阳光像画师魔幻般变换着田园上的色彩, 早稻禾苗由嫩绿变成深绿, 由深绿变成金黄。晚稻插上了, 农田里又青了, 绿了, 黄了。那时节故乡的农田像位爱美的姑娘, 不时地更换着绚丽多彩的新装。
不知哪一辈的劳作者给队上一百多丘田都起了名字, 长的叫长丘, 弯的叫弯丘, 圆的叫圆丘, 方的叫方丘, 一头大一头小的叫锤丘, 一头尖一头扁的叫钻丘, 还有驼丘、扇丘、铜钱丘、银元丘, 那一串蘸满乡土风味的田名描绘出每个丘块的生动形态, 也饱含着乡人对农田深深的爱恋和美好的寄托。翻阅那一叠农田档案, 读着那一串田名, 像欣赏一首农家古老的诗作。
故乡的农田是搭在旷野里的一座大舞台, 一年四季生灵万物在不息地演绎着鲜活的戏曲。农家人们在田园里春种秋收, 粗犷的吆喝号子在田间飘荡。牛群在河渠边山林里觅草, 牧童与牛儿在悠悠对歌,鸟儿在田园上空舞动双翅, 双双对对啼唱呢喃, 山鸡在稻田里亮出美丽的尾羽, 不时传出几声幽鸣。于是, 田园里充满了生机, 一支支蘸满乡土味的交响曲在旷野里回响。
农田是家乡的一部史书, 撰刻着家乡历史的变迁, 记载着它与故乡人们的共同命运。我记事起看到农田中间那条路是用石板铺上的, 数十丘山腰间排田都是先辈们开山凿石造出来的, 田埂背面砌了石头护坡, 顺着山势开有水圳。十多条山冲里上部都开出了山塘。我难以想象, 在那近乎原始的生产条件下, 先辈们靠着扁担锄头完成了田路渠塘如此浩大的工程, 开创出这宏大的基业,不知他们曾流下过多少血汗, 历经了多少岁月, 这难道不是先辈们一部沉甸甸的创业史!
近几十年社会在飞速前进, 故乡的田园也改变了旧的模样。上世纪六十年代, 队上两山之间筑起了一座土坝, 修起了一个水库, 高峡出平湖, 七十年代一条长长的渠道从远处修来, 为队上引来了大型水库的甘泉。“农业学大寨”年代队上拉直了许多弯弯的田埂, 扩大了丘块, 加固了田埂护坡, 增添了田间渠道, 经过几年的“改天换地”, 队上农田“筋骨”更强壮了,“血脉”更畅通了, 焕发出青春活力。
近些年, 田园与屋场里的人们一道跃进了现代社会, 拖拉机代替了蹒跚的老牯牛, 收割机代替了原始的镰刀, 古老的人力水车换成了电动抽水机, 石板路变成了宽阔的机耕道。田园不负农家人的重托, 每亩奉献稻谷由过去一年两熟的二三百公斤到如今一年一季的五六百公斤, 农村实行责任制之后, 故乡的农田年年高唱丰收的凯歌。
故乡的田园里留下过我童年的欢乐,春日我们在水田里捉鱼捞虾,夏日我们给在田里劳作的父辈们送茶递水,秋日我们在田野里放牧嬉戏,冬日我们在原野间玩冰赏雪, 那里,一年四季有我们的足迹, 有我们的快乐, 飘荡着我们童年的欢歌。
高中毕业之后,我回乡加入了田园耕作的劳动大军, 翻田、积肥、插秧、收割, 一年四季, 早早晚晚, 我与田园厮守, 用汗水滋润田园的肌肤, 用辛劳唤醒田园的灵性。那些年我和田园一道合唱着昂扬的战歌。
转眼二十多年, 我又回到了故乡那生我养我的田园, 久别重逢, 我感到它依然是那么熟识, 那么亲切。我抓一把农田的泥土, 芳香依在, 温热依在, 可细瞧它, 感觉它似乎有些憔悴衰老, 山田排田里长满了杂树荒草, 田埂崩塌, 已不见昔日平整光鲜的模样。据说队上四分之三的劳动力离土离乡, 作田的人少了, 已无力打点队上那一百多号水田, 只好忍痛让偏远山田荒芜苍老。都说人生易老天难老, 难道家乡这亘古的农田也会老去吗?
站在静静的田园里, 我想, 千百年来农田用乳汁无私地抚养着家乡的人们, 让屋场里代代生生不息, 故乡的人们对你那么依恋, 那么敬仰, 一定不会让你衰落老去。中央已下达了多个加强“三农”工作的文件, 给乡村注入了强劲活力, 故乡的田园应该是正在蓄势待发, 正在退茧新生, 一场好戏就要上演, 田园里那寂静应该是这曲好戏开场前的短暂肃静。是的,故乡的田园它不会荒凉, 不会衰老, 它永远是一幅迷人的画, 一曲动听的歌, 一首脍炙人口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