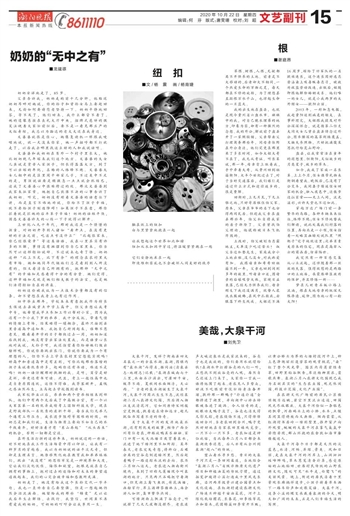■龙建雄
奶奶安详地走了,85岁。
父亲告诉我,奶奶走的前十几分钟,他贴近奶奶耳畔对她说,你的孙子和曾孙女马上要赶回来,无论如何要请您老坚持一下。奶奶平静地回答,等不及了,他们回来,我什么都管不着了。她的遗像悬挂在丧礼大厅中央,招牌式慈祥的微笑注视着大家忙前忙后,要不是一看见那庄严的大红寿棺,我总以为豁达的老太太还在我身边。
文婆婆就很是伤心,她像复读机一样跟我哽咽地说,就一天没来你家,她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以后我去哪里找这么好的人和我说话呀。
文婆婆和我奶奶在另外一个村子里长大,她比奶奶晚几年嫁来我们这个地方。文婆婆的大女儿虽说是贫苦人家孩子,但长得落落大方,到了可以出嫁的年纪,求婚的人络绎不绝。文婆婆大女儿相中的是区里周干部家儿子,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男孩说话要是稍微急一点点就会犯结巴,这成了文婆婆心中很难跨过的坎。那次文婆婆到我家来扯家常,她把自己犹豫不决的心事告诉了我奶奶。听完,奶奶没有顺着文婆婆的话意往下讲,而是直言不讳地劝说,你给不了孩子幸福,就不要给孩子制造障碍!如果孩子不在意,那你拦着就是拦她的后半辈子幸福!奶奶的话短平快,困惑文婆婆许久的心结一下子就得以解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孩童,对奶奶开导别人诸如“看开点,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吃这点亏没什么”“比起张家来,你已经很荣幸”等这类话语,我在心里其实有许多的不解,事情没有摊摆到你自己家里来,你当然可以这样轻松说辞。不过说来也奇了怪,奶奶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理念在农村里大有市场。她和她同年代姐妹们总是看到别人所没有的,但又看清自己所拥有的,把那种“无中之有”的幸福知足感看得十分的有分量。她们觉得,这种幸福知足就是她们相夫教子的法宝,也是她们活得轻松自在的源泉。
奶奶这些被我认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信条,却不曾想在我身上也有过作用。
初中毕业那年,学校本来有意把我作为特长生保送去县城重点中学上高中,但父亲想让我考中专,他希望我早点参加工作以帮衬小家,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我7岁的弟弟。我十分反抗,带着气愤的情绪上考场,结果砸得一塌糊涂,最终只接到县里普通高中通知书。我把自己封闭起来,谁都不愿意见。眼看着开学的日子都快过去一周,奶奶知道后找到我,她没有拿出家法处置我,而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大孙子呀,我还指望着你给姊妹们做出榜样呢,你说你要跳出农门,你说你要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但你不去上学在农村里空想能实现吗?好高中和普通高中是有差别,可你比起那些落榜的孩子来说要优秀许多,起码你还有书读,难道不是吗?奶奶一语惊醒那时执拗的我。是呀,甭管是好是坏,毕竟还有书可读。况且,考上一般性高中也是自身原因造就,这怪不得谁。我茅塞顿开,羞愧之感油然而生,立马赶去学校报到读书。
我军校毕业以后,弟弟和两个堂弟相继来到部队,他们中有两个先后成了中高级士官,有一个以大军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国防科技大学,现在是野战部队一名优秀的连职干部。每当我们兄弟几个遇有工作压力、成长进步阻碍等困难的时候,奶奶总是和我们说,生活与物质上要向不如自己的水平线看齐,好好活着才有“东山再起”“从头再来”的机会,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在外生活打拼的这些年来,奶奶说过的一些话,时不时地在我工作生活场景中得以印证,让我有一种岁月的穿越感。我以为奶奶说的话平淡无奇,但却是至理名言。她潜移默化地在教育我和弟弟妹妹们,跳出“我没有”的思维牢笼是一种境界和大度,它让我们淡化忧伤、悔恨和欲望,把眼光放在自己拥有的事物上,把对过去的追悔和对未来的奢望通通收起来,我们的心定会被幸福和感激所充满。
奶奶走了,她没有给我这个长孙交代一字半句,我也一直劝告自己要坚强,但是一想起她仍然会泪流满面。她留给我的那些“锦囊”足以让我后半生去解悟、去践行。我坚信,世间虽不再有爱我的奶奶,可奶奶的叮咛会让我享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