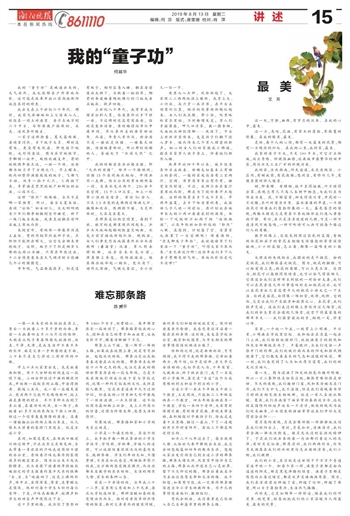一根一米来长的木棍担在肩上,身后一头挑着三十多斤重的白面,身前一头挑着四五片六七斤沉的烙饼。木棍是从院子角落堆柴处挑拣的,端直、干净、光滑,是我生活中不离不弃的伙伴。面是父亲一手新磨的麦子面,三十来斤是自己将近三周时间的口粮。
早上六点从家里出发,先是挑着面和馍,用十几分钟的时间走过一段慢下坡,三四分钟经过干涸的稠泥河床,开始爬一段较长的山路,中途得换肩、歇缓三五次,也一前一后遇见梁山、党湾两个总能听见鸡鸣狗叫、地上满是粪便的村庄。半个多钟头后到了东山梁,在梁顶吹吹风,坐一阵子,再挑着40多斤沉的东西往下拐三四拐,转过一个经常轰轰隆隆的磨房,沿着一溜豁豁拉拉的矮土墙往东走,从几根木头撑着的裂缝门里进去,就是古道小学。
其间,如果是夏天,在肩挑口粮前行的过程中,汗流浃背总是难免的,当我带着一身浓浓的汗味走进简陋不堪的办公室,意味着汗味也要传到裂缝很多的教室里去。因为往往来不及洗脸擦身,北头房檐下挂着的吊铁板就被指定的学生握着约莫半尺长的铁棒“当、当、当”地敲响了,这是上课的铃声,传开去,显得浑亮、厚重,是警醒也是催促,既针对每个学生又针对每位老师。于是,汗味在教鞭声、授课声和学生的回答声中慢慢淡下去。
这十多里的路,我历经了整整四年1460个日子,刻骨铭心。离开那里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条路萦绕我的心头,搅和在自己的骨子和血液里,让我坐卧不宁,醒着清晰睡下不忘。
那条上山下坡、宽一阵窄一阵的土路,如果放在地图上看,就是弯弯扭扭、起起伏伏的线。那条注定让我把青春消磨在此处的路,那条牵系我神经十六年之久的线,也注定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的一段生命线,总是不厌其烦地引领我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就像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或许在别人眼里,它是再普通再平凡不过的印记,但在我的心河里却无形中激起了一丝丝波澜、一点点情愫。这不仅仅因为最初踏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惊喜,还因为珍惜生命,感恩生活的情怀。
形象地说,那条路和家和小学的关系应该是:
小学是一个谋生的结,在这个结上,我手把手教一群流鼻涕的小学生学汉字、学唱歌、学跳舞,学做人的道理,可以说凝结着深深浅浅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学生们年幼无知、不懂事理,不存在如此感受,唯独孤单影只的我,这方面的感觉极其强烈,而这些都来自教学的长长短短、生活的烟熏火燎、家长的各种心态。
家是一个亲情的结,当年我二十一二岁,家里有父有母和三个兄弟,每次从学校返回家,那种温暖如春的感觉便油然而生。面对母亲简单却热喷喷的饭菜,面对父亲亲热的嘘寒问暖,面对弟兄们和睦的说说笑笑,陈旧的房屋虽然昏暗,我感觉身边洋溢着一股浓浓的亲情。这时候,发生在学校办公室、教室和校园里、与学生相关的那些事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结和结之间,就是曲曲折折、弯弯拐拐,我不得不走的那条路。它牵扯着两头、两个结,似乎是宿命,老天早已安排好的;也似乎是人为,十年寒窗、九载熬油,终于跳出农门,成了一名农村小学教师,落定在“古道”这个与我有缘的村庄和这个村庄的小学。
古道小学一共五个年级五个班三个教室,立足现状,只能把二三年级容纳在一个教室,四五年级容纳在另一个教室。学校一共四个老师,大家有时候固定教,有时候穿花教,重视互帮互助,在积极探讨中教孩子们。除我是走着十五里路、翻过一座山、下了一道坡的外乡外村老师外,其他三个都是附近村庄的。
如今二十八年过去了,每当夜阑人静、从俗世凡务中解脱出来后,我总会回想起最初四年的教书生涯,想起从家出发引领自己到古道小学的那条路,那条天晴天阴、风里雪中陪伴自己的土路,那条从此伸进自己心灵世界、留下不灭印记的路,那条扯着我至今乃至永远感恩生命和生活的路。我斗胆想,如果有可能,我一定要将那条路写进当今小学生的教科书,用平凡的事情感染他们、激励他们。
有机会的话,我还要重走已经融入自己生命篇章里的那条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