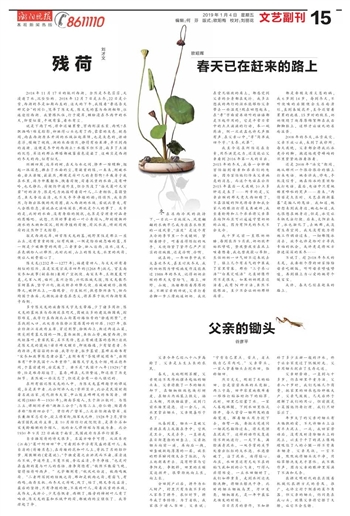2018年11月17日的杭州西湖,全然是冬色茫茫,天浸透了水,沉坠坠的。2018年12月7日是立冬,22日是小雪,西湖的冬是如期而至的。这天的下午,我随着“鲁迅杂文研究会”的同仁,凭吊了陈文龙。陈文龙的墓与西湖相邻,往返途经西湖。我紧跟队伍,行于堤岸,顾盼浸在冬雨中的水天,仰望似霾,平视有雾,看水有尘。
说是下雨了吧,撑伞还嫌累赘,冒雨则湿衣裳。雨呢?在飘洒吗?难觅踪影,却淋得心头也有了雨,蒙蒙的灰色。疑惑间,雨在西湖原本开阔的水域扯起屏障,也是灰色的,游动悬浮,模糊了视线。湖的水面悄然,静得有些呆滞,寻不到雨的涟漪。这便是冬中的西湖么?水槛不但不清,尚多了点滴的忧愁。岸边的那山那塔都被雾霾色浸染了。这确实是西湖的冬天的雨,似有似无。
环顾四周,远岸的树,在天与水之间,撩开一隙幔脚,翘起一抹深色,拂去了水面的尘,有凝重的绿,一束束,刺破水面,若点若缀,簌簌然,那便是荷叶儿的身影啊!半截身子栽在水里,竭力伸展躯体,拽着荷梗,荷着沉重的水面,没有呻吟,也无挣扎。荷梗仍中通外直,但全然没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时的活力,很是吃力地挂碍着荷叶儿,二者相依,柔弱坚忍,虽无香远益清,也不失亭亭净植的韵;悄悄然,我自岿然,勾勒出孤傲的残荷图,嵌入西湖的水域。若说此景美,有人会跟你急,若说品之滋味深长,那就是个人的事了。庆幸的是,此时的水面,没有舟船的搅扰,也算是管理者对品者的恩赐吧。试想,只须好事者的一叶小舟闯入,即刻便撕碎湖水的木纳和深沉,削断净植的荷梗,荷沉水底,顷刻间残荷的淡然即了无踪影。
驻足西湖之岸,回首陈文龙的墓,视野里仅是那么一座山丘,还有重重的绿,似有残缺。一侧是险些被忽略的墓,另一侧是少被捧赞的残荷,二者重合,融入这雨,这水,这天,其色调给人以释然。此时此刻,山上的陈文龙,水里的残荷,便让人刻骨铭心了。
陈文龙(1232年—1277年),福建莆田人。与文天祥有着相似的经历。其是宋度宗咸淳四年的(1268年)状元。官至南宋参知政事(副丞相)兼闽广宣抚使。南宋末年,王朝岌岌可危,元军入闽,福州、泉州沦陷,兴化孤城无援,陈文龙散尽家财募兵,坚守兴化,数次斩杀劝降元使。后城破被俘,拒绝降元,被押北上,一路绝食。行至杭州,执意祭拜岳飞,恸而殉国于岳庙。元朝统治者感其忠义,将其葬于杭州西湖智果寺西侧。
多亏陈文龙的族裔陈天宇先生带路,少了诸多周折。陈文龙的墓地虽与西湖近在咫尺,因被众多的建筑物围截,踪影难觅。我等行至西湖北山街葛岭路伍号的“静逸别墅”,才算找到入口。此处原为张静江寓居葛岭的旧居。1927年,张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穿过别墅,拾级而上,爬过两道山梁,便觅到有墓无园的一隅,墓体斑驳,虽依山势,眺望西湖,但残垣落叶,素若民冢,名不见传,岂止有被遗落的感慨!这就是陈文龙的寝地?若非碑文醒目,即使路遇,少有留意者。冬雨沥沥,有窃窃的私语。我等行者,驻步墓前。墓碑正面书有“宋参知政事陈忠肃公墓”,左则书有“茶陵谭延闿书”,右则书有“中华民国十八年重修”。据陈天宇先生介绍,明正德年间,于墓前建祠,后荒废了。若不是“民国十八年(1929)”重修,怕是难存踪迹了。墓存,碑在,无须赘述,即还原了历史细节。虽然被一些淡忘了,但还是会有一些人铭记的。
在所有铭记陈文龙的人中,为陈文龙墓碑题字的谭延闿,当是其中者。此公何许人也?资料显示,此公是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近代颜书大家、中山陵主碑碑文的书写者。谭延闿(1880年—1930年),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陈三立、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曾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1928年2月,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至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婚姻的介绍人。他的女儿谭祥嫁与陈诚为妻。此公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
自古描写荷的诗文很多,名篇亦唾手可得。从汉乐府《江南》“莲叶何田田”中,可看到水中浮有茂盛的莲叶儿。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荷塘的花和叶儿上,寄托了月的轻纱梦。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也是对鼎盛期的莲与叶儿的感悟。唐李商隐有:“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元萨都刺有:“秋风吹白波,秋雨呜败荷。”二者所写到的枯败之荷,那却是秋雨之荷,有霜飞,有雨呜,尚存生机。而冬天之荷呢,残了,枯了,绝无香远益清,最后的坚持,只有净植的梗,不腐的叶儿,荷着沉重的水域,或伟大,或渺小,少见感慨者。雨稠了,路旁的樟树叶儿有了响动,陈文龙的墓和水域中的荷,都被雨的尘锁住了。我等撑起了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