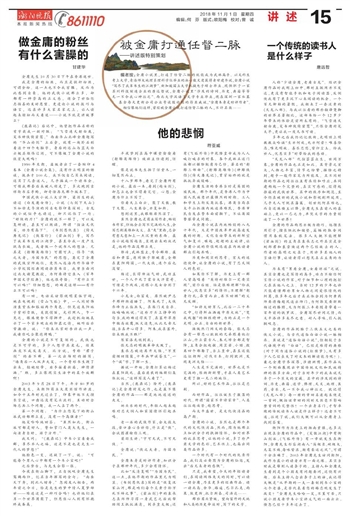半夜梦到在高中课堂偷偷看《射雕英雄传》被班主任逮到,惊醒。
像是说书先生拍了惊堂木,一切戛然而止。
十八岁那年,看完了金庸所有的小说。最后一本,看到《越女剑》,却怎么也舍不得看完它。心想:金庸为什么不写了。
你看天上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想到这里,我眼眶居然湿了。
虽然金庸也是商业写作者,畅销书作家,但他会去写不完满的人生,会写悲剧英雄和大义。在“爽”里面,总会有意无意加上一点沉重的东西。最后小说越写越长,呈现出来的状况是,他的作品没那么爽。
郭靖,武林盟主,号令群雄。最后和黄蓉,连同独子郭破虏,全都在襄阳殉国,一代大侠,连个后也没留。
杨过,长得帅运气好,武功盖世,一个人干死了蒙古大汗蒙哥。可惜是个残疾,还跟小龙女分别了十六年。
小龙女,白富美。居然被尹志平那种狗逼睡了。阿朱死了,大侠乔峰为止住兵戈,在雁门关自杀。他喃喃地说:“这些刀头上挣命的勾当,我的确过得厌了。在塞外草原中驰马放鹰,纵犬逐兔,从此无牵无挂,当真开心得多。阿朱,我在塞外,你来瞧我不瞧?”
陈家洛光棍到底;
张无忌的明教革命失败了;
袁承志被迫离开大陆,“万里霜烟回绿鬓,十年兵甲误苍生”,一个“误”字,了解一生。
据说一开始,金庸打算让杨过在襄阳战死。最后连载的编辑们集体抗议,“这样写没人看了”。
当然,《鹿鼎记》除外,《鹿鼎记》是金庸封笔之作,也是最不像金庸的作品——那是地地道道的爽文。
奶头乐的时代,年轻人越来越难对悲天悯人和家国情怀引起共鸣。
老一派的武侠作家,会大段大段,苦口婆心告诉你,什么是“侠”,会试图灌输你三观。
梁羽生讲:“宁可无武,不可无侠。”
金庸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本身是时评作者,知识分子在那种年代,多少会有情怀。
比如“反清复明”“为国为民”。这一点,在他早期的作品里尤为明显。《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恢复汉家山河,那是咱们每个炎黄子孙万死不辞之事”。《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拜师习得一身武艺之后就帮助闯王抵抗满清,刺杀皇太极;还有《飞狐外传》中乾隆皇帝成为人人喊打喊杀的对象。各个武林正道门派都以驱除鞑虏为己任。著名的“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贯穿始终的就是抵抗异族侵略。
金庸生活的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个年代,是香港人作为中国人民族意识最强烈的时期。工人和学生上街反英抗暴;港英当局在太平山抓捕内地逃港难民,香港市民自发在警车面前躺下,不让英国警察带走同胞。
而金庸小说在内地畅销的八九十年代,又是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时期。文化自由带来的新鲜空气和复兴、崛起、赶超的主旋律,让金庸小说的价值观迅速在内地读者群众引起共鸣。
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宏大的道德使命,让金庸的小说,有了悲天悯人的色彩。
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上有一群人曾高唱着“英特耐雄尔一定要实现”,前仆后继。怕是很难理解“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情怀;不理解“躬身行礼,昂首而出,再不回顾”的义无反顾。
“如许大好男儿,此后一二十年之中,行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焚我残躯”的牺牲精神,为的正是一个光明、公正、自由的新世界。
换做热门网文的套路,张无忌会有一帮忠心耿耿的兄弟跟着他打江山,什么蒙古人、朱元璋全都是智障,主角会把赵敏、周芷若、小昭、殷离四个都娶了,当上皇帝,甚至还能远征朝鲜、讨伐日本、打到欧洲、发现美洲大陆……
人生是不完满的,世界也是不完满的,维纳斯断臂,才在人类艺术史有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所以,好的艺术作品,往往是悲剧。
而好作品,往往诞生于激荡的时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人类往往越痛苦,越思考。
而太平盛世,是文化快消品的高产期。
金庸的小说,当然也是那个年代的文化快消品,然而,因为他那么点知识分子的执拗情怀,和对世界的认真思考,让他的小说,多了些严肃文学的色彩,艺术性上,也高出同类作品许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我们没必要因为金庸的仙逝,发出“后无来者的感慨”。
只是,我希望,今天的年轻读者们,在阅读网络爽文的同时,可以读一读金庸,乃至更多的经典作品。读一读北岛、余华、路遥、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司汤达……
那些眉头紧皱,望向窗外的天地和人类的历史命运时,写下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