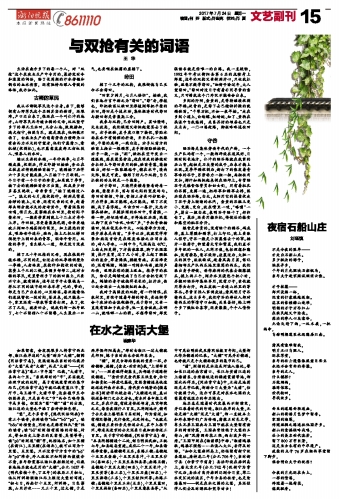如果留意,会发现很多人将常宁西北部、湘江南岸边的“大堡”称为“大铺”。翻阅《同治常宁志》,发现该地在当时的记载并非“大堡”或者“大铺”,而是“大浦”——《同治常宁志》“卷三·市亭篇”记载,“大浦市,县西七十里。”当然那时的“市”,其实就是治理市政的处所,属于有规范管理的集市而已。《同治常宁志》中就记载有蓝江市、官厅市、马王塘市、大浦市等,这些墟市至今仍然存在,只是当年之“市”而今已唤作集市或乡镇。但因为“堡”“铺”“浦”的出现,湘江边的大堡也平添了些许神秘色彩。
“堡”,是个多音字,《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三个读音,分别读作“bǎo”“bǔ”“pù”。读“bǎo”时指堡垒,同时也是稀有姓氏“堡”姓的读音;读“bǔ”时则指有围墙的村镇、村庄,譬如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吴堡等等;读“pù”时则通“铺”字,纯指地名,如十里铺(在浙江)、五里铺(在湖北),就可以写为十里堡、五里堡。只不过常宁方言中的“bǔ”与“pù”难分,外人往往不知所措而傻傻分不清,当年徐霞客从湘江乘船经过时,记载当地地名就也是用的“大铺”。公元1637年(明代崇祯十年、丁丑年)的农历三月初七,他从河洲驿溯湘江而上经过大堡时写道:“初七日,西南行十五里,河洲驿。日色影现,山冈开伏……又三十里,过大铺,于是两岸俱祁阳属矣。”那时由湘江一过大铺就是祁阳,缘于当时尚未分设祁东县。
“铺”,则是古驿站系统的重要一环,亦称铺驿、递铺。《金史·世宗纪》载,“上谓宰臣曰:‘……朕尝欲得新荔支,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金世宗是金代第五位皇帝,估计和杨贵妃一样爱吃荔枝,竟然靠铺递来快速运送这种南方水果。清代黄六鸿著的《福惠全书》则讲得比较全面:“夫铺递之设,盖以供送各衙门之公文者也。有本州县申报上司之文,其在冲途,有彼省传送邻省,及京部院之文,每昼夜须行三百里。凡所到地方,铺司于公文套上填明某日某时到,即为前送,如有稽迟擦损,定行查究,此定例也。”也就是说,铺递主要任务是传送公文,其中上报市州、跨省及进京的公文还要日夜加班传送三百里。关于常宁的铺递,《同治常宁志》称,“本县所辖铺递十二处,创自明洪武初。正统七年,知县赵忠重建。成化二十一年,知县谢廷举重修。总铺铺司五名。东路三铺:总铺起十五里至金塘,十五里至东冲,十五里至沙江(各四名),十五里至耒阳县界;南路五铺:总铺起十里至大陂(四名),十里至长冲,十里至黄茅(各三名),十里至石盘(四名),十里至弥勒(三名),十里至桂阳州界;北路三铺:总铺起十里至玉水(五名),十里至蓝田,十里至柏坊(各四名),十里至清泉县界。”从中可见由明洪武至清同治数百年间,大堡都无作为铺递的记录。“大铺”可见并非铺递,也许就只是个大铺面较多的集市而已。
“浦”,则指的是水边或河流入海处。譬如长江边的南京浦口、长江与黄浦江边的上海浦东、台湾海峡边的福建霞浦等地,都因此而得名。《同治常宁志》中,无论是地图还是文字记载,都称今日大堡为“大浦”,估计就源于此,这亦可算是对在水之湄的大堡最有说服力的命名缘由。
地名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并记录着时代的印迹。湘江南岸的大堡,无论是称“大铺”还是“大浦”,都一直被本土和外来游子们广为传颂。清雍正时邑文学、孪生兄弟王国典与王国甲就在大堡留有诸多的绮丽诗篇,王国典曾惊艳于大堡的玉荷山,称“风清涧曲花三径,雨打溪声钓一湾。”王国甲则在《湘浦歌》中称:“湘浦鸿雁秋,鸿雁不须愁……北流入大江,吾得及时游。”如今大堡麻洲岛上,仍保留有新宁故县遗址。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当时新宁县(今常宁市前身)县治即设在麻洲岛上,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新宁为常宁之后,县治才离开麻洲迁到今日宜、潭二水交汇处的城区,千年古县的往昔,也是沧海桑田——倒是在水之湄的大堡,真还值得人们去及时游玩和凭吊访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