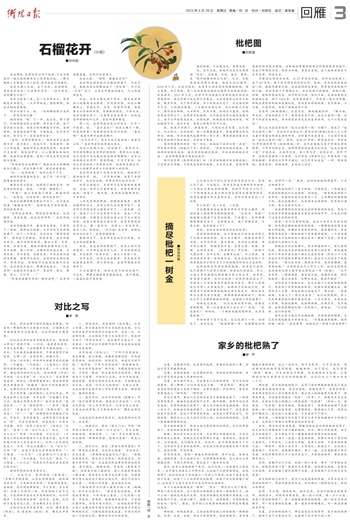■罗 平
浅夏,是春的归宿,也是夏的起程。有榴花扶摇的心事,在这个季节里激情燃放。
浅夏,是春的落款,也是夏的封面。有枇杷成熟的酸甜,在这个季节里结成故人愁绪的回味。
浅夏,家乡的阡陌上,行走着农人忙碌的身影。家乡天空的雨雾里,有一群群一行行的鸟雀在飞舞。“布谷布谷”,那是布谷鸟在催促着农人莫误了耕耘。也有竹鸡在一声声啼叫,像是在夸赞着农人“耕作快”“耕作快”。
在这个季节,最让人忆念的还是家乡的枇杷成熟了。一树树金黄的果实,掩映在浓密的绿叶之中,格外耀眼。母亲多次打来电话说,家里的枇杷已经黄了,要儿女们抽空回家摘枇杷,再过一些日子,枇杷就会熟透掉落了,也会被鸟雀啄吃了。这是居住在乡下的母亲,在这个节季里的牵挂,如同这个季节的天气,时雨时晴,难免让人心生几分归乡的心动;如同成熟的枇杷,总有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
家乡的枇杷熟了,熟在江南浅夏的微风细雨里;家乡的牵挂浓了,浓在枇杷成熟的季节里。
枇杷,犹如家乡的父老乡亲,总是那么的随遇而安。不管生存环境怎么艰难,枇杷总是生长得那么旺盛。房前院后,渠边沟边,山岭坡地,它们随处生长。近些年,家乡的枇杷树多了不少,大部分不是乡亲们栽种的,而是鸟雀啄食枇杷果后留下的籽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老家的房前,曾有一棵高大的枇杷树,绿叶如盖。每到浅夏,满树金黄,令人直咽口水。记得那株枇杷树,是父亲从山里移植来的。不到几年时间,便长成了一株亭亭大树。
夏天,全家人在枇杷树下乘凉。我们兄妹,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一边听着父母讲天上牛郎织女、七仙姑下凡的神话传说。在枇杷树下,我们还知道了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知道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知道了二十四孝的美德故事,知道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也知道了父母日出而作日息而归的生活滋味。
乡下人把枇杷树视为“树神”“药王”。哪家老人患了哮喘,哪家小孩头痛发热,大人便会从枇杷树上摘来一把枇杷叶子,把叶上的一层绒毛用清水洗净,然后用铁锅或者药罐子煎熬成一大碗枇杷叶子汤,让病人服下,连服几日,病竟痊愈。又因枇杷成熟就如“金丸”,因此,家乡的人们便将枇杷树视作财富和健康的象征。
那时候,枇杷成熟后,父母会把掉在地上的枇杷果一颗颗捡起,洗净,去皮,去核,用文火慢慢熬煮,制成枇杷膏,再用玻璃瓶子装好密封,放上一些时日,既可当药用,又可当食品。母亲熬制的枇杷膏晶莹剔透,酸酸甜甜。为了贪吃,我们常常“捏怪”撒谎,不是说脑壳不舒服,就是喊喉咙又发痒。父母便会从柜子里拿出宝贝似的枇杷膏,让我们吃上一两口或者一小勺。
那时候,家乡的枇杷树很少。我家门前的那株枇杷便成了周边邻居羡慕和垂涎的目标。每当初夏时,枇杷成熟了,金黄金黄的,母亲便安排我们小孩子驱赶鸟雀,莫让鸟儿把枇杷果实啄食了。母亲很贤惠,知道谁家的媳妇“巴肚”(怀孕)了,枇杷还未完全成熟时,就要我们爬上树摘上一两把送给“巴肚婆”(孕妇)吃。母亲说,“巴肚婆”喜欢吃酸的。枇杷成熟了,母亲便会把摘下来的枇杷一份一份地分送给邻居。也有嘴馋的,偷偷摘上几吊。母亲也会叮嘱我们:就让别人去摘点吧,千万莫惊吓了别人。
那时候,一树枇杷不但代表了家乡父老乡亲的酸甜日子和烟火生活,也体现了邻居之间那浓浓的纯朴情感。
后来,因为老宅改造重建,那株伴随我成长的枇杷树没有了。我又在院子周围栽种了好几株枇杷树,如今,都已开花挂果。由于生态环境好了,家乡随处可见一株株挂满金黄果实的枇杷树。
回到家乡,采摘了一篮篮一筐筐的枇杷,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儿童时代,少年时光,心里有几分酸,更有几分甜。可母亲却叹着气说:“那些年,村里小孩子多,又冇得吃,枇杷又少,生怕别人莫偷摘了。可如今,枇杷到处都是,黄了一遍,总等着盼着小孩子来摘,但农村都冇得几个小孩子在家了。多好的枇杷呀,硬是好哒那些鸟儿……”
是啊,鸦鹊声欢人不会,枇杷一树十分黄。那个“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的唐代才女薛涛,你的桥边枇杷,是否也已经成熟,是否酸甜了唐代的那个浅夏,是否酸甜了历代的才子与墨客?
家乡的枇杷已经熟了。有多少白发苍苍的爹娘,正等在老家门前的枇杷树下,浑浊而昏花的目光,如同烟云一般飘向远方,飘向山的那边。
我啊,多么想,抽些时间,抽点空闲,在这个枇杷成熟的季节,回到家乡,回到母亲的身旁,搬一把小竹椅,架一方小方桌,坐在门前的枇杷树下,尝一尝酸酸甜甜的枇杷果,赋一阙五月的南歌子,听一首古典的琵琶曲,望一望家乡的鹧鸪天,哼一曲湿漉漉的声声慢……
浅夏,家乡的枇杷熟了,那是鸟雀欢乐的季节。家乡的枇杷黄了,酸甜了这个浅夏的五月,也酸甜了远方游子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