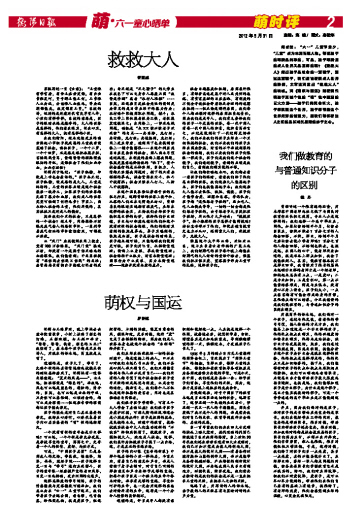记得女儿两岁时,晚上带她去岳麓书院前散步,小树上挂满了彩色的灯珠,五彩斑斓。女儿脱口而出,“爸爸,爸爸,快看,彩色的玉米!”我惊讶了,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用现在的话来说,简直就是太萌了。
遗憾的是,孩子大了,学习了,充满个性的纯真诗情逐渐地被模式化的测试卷给磨灭了。记得她有一道语文填空题:“夏天的风是——”,女儿说,标准答案是“绿色的”。而我说,风也可以说是蓝色的,蓬松的,清香的,当然,也可以说是云朵的呼吸,只要你可以感悟到、心领神会的,都可以成为答案……但这些奇妙的答案都让孩子摇头否定。
孩子的摇头是对自己真正感受的否定。我好生心疼啊。心疼代表着孩子内心真实感受的“萌”性的逐渐消失。
一个没有萌性的童年会是什么样呢?可以说,一个个性是否充分发展、是否被尊重的童年,冥冥之中,定夺着一个人的性情、爱好、处世方式。
可是,“中国孩子真累”已是各国友人的定论。学奥数,读英语,练琴,画画,敲架子鼓……孩子这样日复一日与“学习”进行生死搏斗,孩子的童年像一架磨损严重的老旧风琴,日复一日地转动,发出沉闷的吱嘎声。
这样高强度的学习训练,孩子的情感指数与笑容指数可想而知。我们总以为在“六一”儿童节这天,我们带着孩子去逛公园,看电影,吃肯德基,给他买礼物,就是爱孩子,但这短暂的、片刻的温暖,像夏日清凉的风,稍纵即逝。更多时候,这种“爱”变成了赤裸裸的绑架,因为我们成人世界本身也被这个社会的“名利场”给异化了。
我们生活在物欲统治一切的社会环境中,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们只顾指责体制与他人而不反省自己……我们所有的人都习惯了这个社会扼杀孩子童年天性的既成规范与制度,以成全它的运行。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其推动者与同谋者。
我们教导孩子学雷锋,可有几个大人学会了主动让座?我们教导孩子要爱护环境,可满大街的垃圾难道全是小朋友的杰作?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来。理想中的教育,最终被现实社会中大人们急功近利的“不诚实”给彻底抵消了。救救孩子,必须拯救大人,改造成人社会。这样,我们或许为拯救孩子寻找了一点出路,这,才是真正的长远出路。
孩子的内心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一样纯真,丰富无比,有着自己的意见和声音,而成人需俯下身子去倾听,对于自己听到的那些意见和声音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每个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来对待。而享有足够的重视、尊重和呵护的生命,也一定会用这样的姿态去对待所有的生命,这将是一个十分令人憧憬的美妙循环。
遗憾的是,许多成年人都没有意识到和做好这一点。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怪圈,被套进去后,被惯性带着,匆忙、懵懂甚至是无知地往前走,等到醍醐灌顶的那一天,猛醒过来,才发现孩子已长大了。
1925年8月的瑞士日内瓦儿童福利的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国际儿童节”的概念。自那以后,保障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等各项权益成为各国政府努力要做的事情。可是今天,在中国,我们还是要再加一条:给予孩子们萌权,尊重他们的天性。因为,这些才是实现上述权益的先决条件。
要做到这些,对于中国当下的教育来说是多么艰巨而迫切的任务。说厉害了,这涉及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涉及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幸福指数。国民素质低下决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教育等制度作出全面的、真诚的反思。
当一百年前我们仍坐在四大古发明的枕头上睡大觉时,蒸汽运动的汽笛已经驶进了东亚病国的港湾。当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还在津津乐道有四大古发明时,我们已不知不觉成为最大的制造大国,而不是最大的设计大国——有着各种环境污染和山寨的制作大国,而不是能带来各种低碳环保、产品增值的创新设计的设计大国。不要说友国人民多么有创造力,环境优美,经济发达。我们需要去检讨的是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直在扼杀儿童的天性,在扼杀人之初的天性。
说远了去,用写诗的人的话来说,赤子般的人的天性具有与黑暗对峙的无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