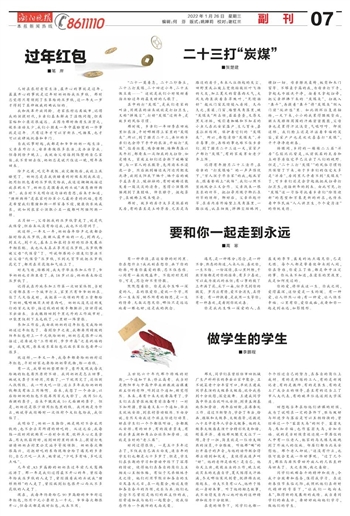■笔 岸
儿时在农村老家生活,最开心的事就是过年,最最开心的事就是过年时奶奶给我压岁钱。那时总觉得只有领到了长辈给的压岁钱,过一年大一岁才得到了某种权威的确认似的。
我和改革开放同龄。老家农村远离城市,记得我的孩提时代,乡亲们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离富裕和小康还很遥远。正因为那时物质生活贫乏,娱乐活动太少,我们小朋友一年中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过年。只有过年才可以穿新衣、吃糖果,也才可以放肆地玩耍和串门。
自我记事时起,我都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亲在外打工,母亲要做很多农活,没办法管我。但每到除夕晚上,我就由父母接到隔壁的自己家住,我不肯回去住,奶奶总是说只住这一晚,明年再回来。
除夕之夜,吃完年夜饭、放完鞭炮后,我就上床睡觉了。奶奶总是在我快睡着的时候来到我床边,把用红纸包着的压岁钱交给我,我迷迷糊糊地接过放在枕头下,奶奶总是摸着我的头说“满崽猪样狗样”。我当时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猪样狗样”是农家对孙辈小儿最朴素的祝福,意思是希望我们像猪和狗一样百毒不侵,健康快乐地成长,就如同农家小孩取小名一般都叫阿猫阿狗一样。
正月初一,父母把我的压岁钱拿走了,说是代我保管,但后来从没有给过我,我也不记得问了。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奶奶每年除夕之夜都会按时给我压岁钱,数额从最开始的一元,到两元,到五元,到十元,基本上和农村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我也从未真正享用过压岁钱,压岁钱都被父母“代保管”了。听说邻居的小朋友们坚决不让父母“代保管”压岁钱,不到元宵节就把压岁钱花完了,都用在买花炮和气球上了。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爷爷奶奶也日渐衰老了。我18岁以后,奶奶再未给过压岁钱了。
记得我在外地参加工作第一次回家休假,当时父母都在另一个城市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在。住了几天临走时,我把第一次领的所有工资都给了奶奶,嘱咐她买点好东西吃。奶奶从没见过新发行的百元大钞,接过钱的时候手都颤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当我辗转回到千里之外的工作城市时,口袋里仅剩下五毛钱了,心里好一阵紧张。
参加工作后,我由收奶奶的过年红包变成给奶奶送过年红包了。每到除夕之夜,我都要用精致的拜年红包封上一千元钱给奶奶,奶奶总是很开心地接过,还要说句“工作顺利、步步升高”之类祝福的话。我发现,原来送长辈红包比收长辈红包要开心很多。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每年都要给奶奶封过年红包,平时回家也要给奶奶带礼物,给一些钱。
有一次,我帮奶奶整理柜子,意外发现我每次给她的红包居然原封不动。我问奶奶是怎么回事,她说大票子不好用,用散了,一下就用完了,还怕别人找假钱。我一听大吃一惊,这么多年我给奶奶的钱都没有派上用场啊。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以后给奶奶的红包不能再用百元大钞了,改用50元面额的票子,后来干脆改成10元面额的票子。但是,奶奶还是很少动用红包里的钱。我问她是为什么,她说等我结婚时一次性封个大红包给我,我怔住了。
我明白了,奶奶一生勤俭,她是绝对不会乱用钱的,也不会去买所谓的好吃的。从这之后,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购买一些时令水果、饮料点心之类食品,用大纸箱封好,送到回村里的班车上,提前打电话请奶奶去村里公交站亭等候领取。奶奶每次都很高兴,还把好吃的东西现场分给了遇见的乡亲们,自己只吃一点点,她常说,“少吃多有味,多吃没点味”。
几年前,83岁高龄的奶奶在过年前几天驾鹤远游了。那一年是我们过得最不开心的年。曾经每年给我压岁钱的人走了,曾经摸着我的头说我“猪样狗样”的人走了,曾经收到红包很开心而从不多花钱的人走了。
现在,我每年仍要给已90岁高龄的爷爷封过年红包,仍用十元小票封上一千元。爷爷每次都很开心,但每次都是收好红包,从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