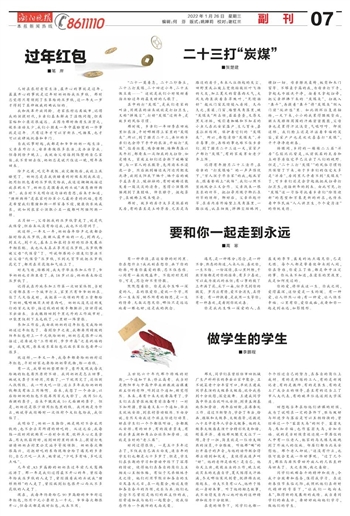■贺楚建
“二十一莫着急,二十二炒蚕豆,二十三打炭煤,二十四过小年,二十五做豆腐……”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掰着指头盼过年的最美好的儿歌了。
其中的打“炭煤”,是我们老家的叫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扫卫生,又称“掸埃尘”。打好“炭煤”过新年,是故乡的风俗习惯。
那时候,乡亲们一年四季在田地里忙农活,平时哪顾得上家里的“炭煤灰”。所以,到了腊月二十三,再忙的乡亲们也会停下手中的农活,开始打“炭煤”。住房灶屋、鸡舍猪棚、墙脚角落以及牛栏,都要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如是晴天,家庭主妇们还会拆下被褥窗帘,与一家人的衣服等,先用淘米水浸泡一会,然后挑到塘边或河边用肥皂洗净,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后的被子盖在身上,暖融融的,有时被褥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惹得小孩像馋猫闻到了鱼腥味,伸长脖子,挺起鼻子,在被褥上吸来嗅去。
那时,故乡的房子大多是低层的瓦房,有的甚至是土砖茅房。尤其是马路边的房子,车来人往扬起的灰尘、田野里或山坡上焚烧枯枝烂叶飞扬的火灰,加上夏天的雷暴雨天气,大风大雨裹挟着杂草败叶,“见缝插针”般从门窗瓦缝侵入房间。久而久之,屋梁、门窗、墙壁及角落里,被“炭煤灰”所占领,层层叠叠,又厚又黑又污垢,吸引着蜘蛛和不知名的小虫儿在此安家落户、生儿育女,甚至拉丝结网,保护着它们的“炭煤灰”。所以,要想清除“炭煤灰”,并非易事。但,再难的事也难不住乡亲们。到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打“炭煤”,有的家庭男女老少齐上阵。
记得有年腊月二十三清早,在母亲的“打炭煤喽”的一声声催促下,“穷人孩子早当家”的我,起床穿衣,跟着爸妈上“战场”。我们心照不宣地既分工又合作。父亲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把扫帚用绳子绑扎在竹竿的顶部,绑好后,父亲举起竹竿,在房内房外墙壁上及角落里,一路往返,认真细致,掸拂尘垢蛛网,横扫一切。母亲擦洗桌椅、板凳和木门窗等。不够桌子高的我,为母亲打下手,拿起毛巾搓洗干净,接着又拿起扫帚,把父亲掸拂下来的“炭煤灰”,扫拢入“粪斗”,再提着“粪斗”将“炭煤灰”倒入门前“坑淤氹”里。如此循环往复连轴转,一天下来,小小的我累得腰酸背痛,额头及脖颈周围的汗珠密密匝匝,父母亲也是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即使这样,我们脸上还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家家户户也是欢欢喜喜打“炭煤”,干干净净迎新春。
转眼间,乡村的一栋栋二三层“洋房”已经比比皆是,从前低层的瓦房和土砖茅房住宅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二十三打‘炭煤’”的风俗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由于乡亲们的住宅大多是“洋房”,房间里几乎看不到“炭煤灰”了,可乡亲们还是会拿起拖把或扫帚打扫卫生,迎接新年的到来。由此可见,打“炭煤”这一习俗寄托着乡亲们“除陈迎新”的愿望和万象更新的祈求,也传承着中华民族“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