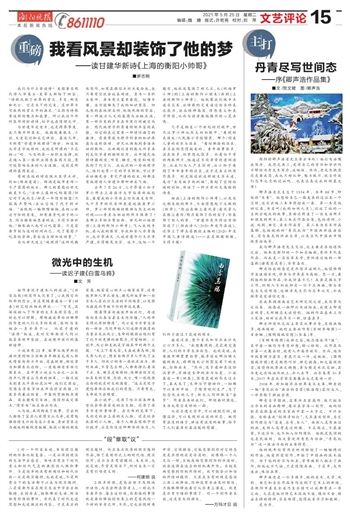■文 芳
按作者迟子建本人的说法,“《白雪乌鸦》的写作太沉重了,心底因它而积郁的愁云,并没有随着最后一章《回春》的完结而彻底释放……”可见,其深深融入了作者的太多真情实感,同时也可以理解,那场瘟疫带给回顾那段历史的人们太多的伤痛,感叹与哀婉会一直并存于心。而迟子建的“温情”叙述,是对灾难面前人何以能在苦难中坚挺、在逆境中前行的最好诠释。
小说共有22章。故事从俄罗斯经满洲里到哈尔滨贩卖旱獭皮毛商人猝死傅家甸街头开始。清盛时期,朝廷曾为加强东北边防,一度鼓励老百姓迁居东北。其中有小说主人公之一山东德平人傅宝山兄弟的祖辈,一路迁徙来到东北平原松花江畔。他们定居后,凭借自身医学功底开设诊室药铺,行医卖药兼治牲畜、开客栈货摊贩卖商品。商业圈吸引百姓,慢慢形成定居点,“傅家甸”地名由此形成。
人与城,共同构成了故事。引出的人物除了富庶人家傅宝山兄弟,还有勉强维持生计的马店小老板、身世贫寒沦为娼妓的粮栈老板娘、孤寂心傲的胡匪家属、极富爱心的点心铺家庭等,还有俄罗斯人罗扎若夫、谢尼科娃等和一些日本人在此讨生活的不同场景,以及因为瘟疫而导致不同的命运发展。
随着傅家甸瘟疫开始流行,再逐渐向东北各省甚至关内传播,“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恐慌中的人们选择用微薄的力量去反抗死亡,生命的脆弱让他们有了比平时更强的凝聚力,守望相助。小说中,死亡和生机是穿插其中的两个主题。“天上下着大雪,又盘旋着乌鸦,每天有人死亡,傅家甸两万多人中死了五千多人。但死亡的另一面就是活力。面对疾病,不管怎么样,人都要挣扎着活下去。生,确实是艰难的,谁都会经历突如其来的灾难、恐惧、死亡,唯一能战胜这些的就是对生的渴望。”这正是迟子建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思想:只要有光,生命就不会绝望。
在小说中,还原了哈尔滨各种类型社会阶层家庭的众生相,还原了很多历史珍贵场景。在灾难的笼罩下,无论是社会上层的大人物,还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每个人都在艰难中前行跋涉,正是依仗这种群体的活力,人们终于渡过了鼠疫的难关。
瘟疫过后,整个东北和华北共计死亡六万多人。“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然而,迟子建却在这份沉重中,穿插进生命的活力与爱。小说最后一章《回春》,寓意鼠疫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生命与宁静回归,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于晴秀顺利生产,为了纪念死去的儿子,新生儿同样取名“喜岁”。作者在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困厄,生活也有它美好的一面。
从迟子建文字中,可以读到悲悯,读懂温情,可以发现对流逝的怀恋。她用有温度的语言,讲述有温度的故事,给予了人们最质朴最温暖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