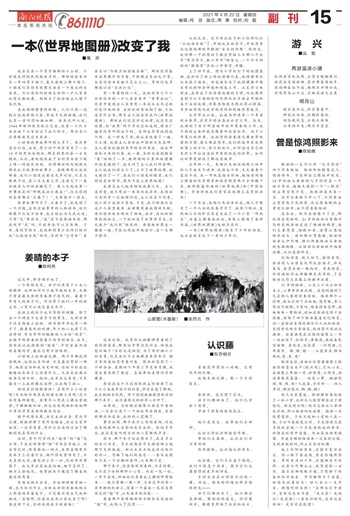■笔 岸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偏僻的小山村。小时候农村的民风极其淳朴,那时的农家白天一年四季不锁门,夏天连晚上都不锁门。小朋友们在村里就像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家庭里,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任何一户人家里玩得天翻地覆,到饭点了就会被主人留下来吃饭。
在我稍稍懂事的时候,人们只要一谈到打仗就特别兴奋,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也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后来还听人说,1944年衡阳保卫战打完后,还有一小队日本兵南下行军经过了我们村子,有些老人还亲眼看见过日本兵。
小时候战争故事听到太多了,居然梦想去打仗。后来,有个村干部家里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是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从此,看电视就成了全村男女老少晚上唯一的娱乐活动。记得那时的电视剧大都是抗日战争的故事片,每晚都有打仗的场面。我们小朋友边看边大声讨论,可是太晚熬不住,第二天又要上学,没看完下一集就被家人叫回去睡觉了。第二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问“昨晚我边打赢没?”,往往得到的答案都是“打赢了!”,又要高兴一整天。
战争故事听多了,又看多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没见过故事里的人物读书,他们好像只打仗不读书。我当时认为文武之道,只有“文”要读书,“武”是不需要读书的。那我就学“武”吧,不读书也可以当英雄。于时,每到节假日,我就和村里小伙伴们结伴玩“山地游击战”游戏,自封为“总司令”,美其名曰“为保卫祖国做准备”。那时农村基本没有课外书可看,平时课业负担也不重,大家对读书普遍不怎么上心,男孩们大多都想以后“当兵打仗”。
有一年暑假的一天,我和村里几个小伙伴结伴到一户人家家里开“军事会议”,无意中发现这人家里有一本我从未见过的彩色印刷的书。当时就好奇地翻了翻,不知道是什么书,那家主人就告诉我叫《世界地图册》。那时我们还没学过地理,也没见过地图,但“世界”两个字还是知道的,因为广播里经常听到这个词,老师也常常说到这个词。我一时来了劲,就认真地看了一遍,不太懂,就请主人告诉我中国和日本在哪。主人很快就翻到书中的亚洲部分,指出中国和日本的位置。我一看,当时就感到脑袋“轰”地响了一声,被两国的位置和版图强烈地震撼到了。我又问了主人我们村在哪,主人说我们村太小了,上不了世界地图。我又被惊了一下,在我们小朋友的眼里,我们村就是世界呀,居然不能上世界地图!
我请求主人把书借给我看几天,主人没同意,说只有这一本书怕我弄坏。我保证不弄坏并一定按期归还,主人还是不同意,说小孩子说话不算数。于是,我只好每天来这户人家里看书。我好像有看地图的天赋,居然很快就弄明白了陆地、海洋、岛屿和国界线的标志,一下就知道了世界有多大,是无数个“我们村”组成的。要想把世界走一圈看一遍,可能从现在开始进行,这一生都不够用。
从此之后,我不再沉迷于和小伙伴们打“山地游击战”了,开始认真地学习,开始思考远远超越那时年龄的“巨大的问题”。特别是,我仿佛一下就明白了教室黑板上方那八个大字“努力学习,振兴中华”的含义,一个不可抑制的“强国梦”在我心中孕育、升腾。
上了初中后,因为小学时打下的地图基础,我担任了班上的地理课代表,地理课考试从未低于满分,并受邀参与了地理课期中期末考试的部分命题和阅卷工作。正式学习地理后,我养成了经常看地图的习惯,对地图熟悉到可以不借助任何参照而徒手画出中国和各个省的地图,形象思维能力因此得以提高,并开始慢慢形成宏观思维和战略思考能力。
大学毕业以后,我成为村里第一个考录的公务员,在家乡的县委办公室工作。后来,我调到了家乡所在城市的市商务局工作,这个局的主要职能是服务开放型经济。由于工作岗位的性质,我继续保持着每天看世界地图的习惯,每天都在思考,我们的城市在世界地图上的方位、区位和地位,如何通过自己的本职工作让这座城市更快地走向世界,如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这座城市。
去年的一天,表姐打电话说她刚上初中的儿子成天不读书,成绩也不好,天天抱着个篮球不放。我一听就直接告诉她,把他房间墙上贴着的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照片全部撤下来,挂两张最新版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并告诉他我们老家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
一个月后,表姐打电话告诉我,她儿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发奋学习了。我登门验证,发现她儿子的卧室简直变成了一个小型“作战室”,书桌上摆着地球仪,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世界地图册》也赫然在列。
一本《世界地图册》改变了少年时的我,也正在改变我下一辈的少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