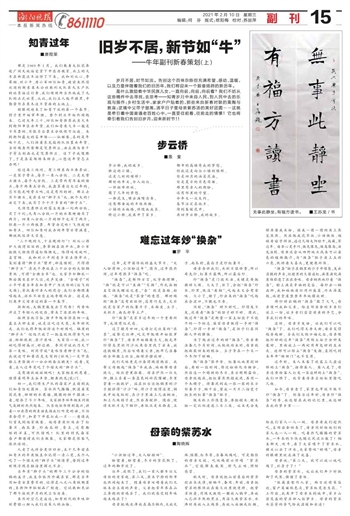■罗 平
过年,是中国传统的盛大节日。“大人盼莳田,小孩盼过年”。因为,过年很热闹,过年有很多“换杂”吃。
“换杂”,是衡阳方言,从字面理解,“换”就是可以“互换”“交换”、作礼品相互交换或赠送之意,“杂”就是杂粮、粗粮。“换杂”就是“零食”的意思。那时候的“换杂”没有旺旺饼,没有巧克力,无非就是自家产的红薯片子、米面皮、豆子、米糕片、南瓜籽等土产。
炒“换杂”是家乡过年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很有仪式感。
过了腊月廿四,父母打完灶屋的“浓墨”,送祭完灶神,吃完中饭便开始张罗炒“换杂”了。母亲开始搂柴生火,把先年炒得乌黑的河沙从角旮里找了出来,放进铁锅里,然后吆喝着父亲,把早已准备的全部搬上灶台,按顺序摆放好。
我们兄妹更是兴奋得跑前跑后。我帮父母搬起“换杂”半成品,妹妹帮母亲烧火,给灶堂里添柴。母亲俨然一位大师,腰上系着一条蓝色的碎花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铁铲,站在灶台边把锅里的沙子搅拌得“沙沙”响。待沙子烧得滚烫,锅底开始发红时,在沙子里滴上几滴桐油,加上几块桔子皮,然后再搅拌。随后,便将米糕片先下锅炒,再依次是米面皮、豆子、南瓜籽,最后才是炒红薯片。
母亲告诉我们,米糕片很娇贵,所以要先炒,红薯片最贱,所以最后炒。
炒“换杂”是门技术活,关键是要把握好火候。火大了,旺了,会把“换杂”炒焦、炒黑,既没“看相”,吃起来又会有苦味。火小了,暗了,炒出来的“换杂”吃起来会涩口,不脆也不香。
同时,“换杂”好不好吃,炒得发不发,还要看“换杂”的胚子好不好。因此,做过年“换杂”是衡量一家主妇能干不能干的一个标志。谁家母亲做得一手好“换杂”,炒得一手好“换杂”,是孩子们在同龄人中的骄傲。
为了做出过年的好“换杂”,母亲要准备几个月时间。从秋收结束时,母亲就把收获回来的糯谷、豆子等在一个又一个冬阳下晾晒。
做“换杂”很辛苦。红薯从地里挖回后,要晾一段时间,待淀粉转化为糖分,然后选一个晴好的冬日,东方刚刚露白,母亲就起床,把红薯蒸熟擂成泥,再用一个木模子,将薯泥刮成一张一张的长方形薯片子,晒干后,剪成一片片二指宽寸把长的红薯“换杂”胚子。
做米糕工序很复杂,要把糯米、粳米按一定比例浸泡三日三夜,让米充分发酵再磨成米粉,揉成一团一团的再上蒸笼蒸熟。然后做成花草状、小动物状、福禄寿禧字样状,通过几场太阳晾干,收藏,等过年。母亲心灵手巧,做兔像兔,做鸟像鸟,活龙活现。母亲还会从田野地头找来可以染色的植物捣汁,为“换杂”胚子染上五颜六色,既好看又喜庆,更健康环保。
“换杂”胚子在锅里的沙子中爆裂,发出清脆的声音,灶膛里的火苗通红,满屋满院满屋场弥漫了浓浓香味。母亲娴熟地炒着“换杂”,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每炒出一锅品种,我和妹妹连忙用竹簸箕、竹米筛装起,端进堂屋整整齐齐地摆放好。
待炒好出锅的“换杂”歇了火气,母亲便叫我和父亲,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送上一份,让乡亲们尝尝母亲的手艺,分享我们的年味。
这时,母亲才发话,让我们可以吃“换杂”了。我们吃得又香又甜,母亲笑得越香越甜。当我们大饱口福之后,母亲便把炒好的过年“换杂”用陶土坛子分种类装好,里面放上一两砣用布包好的生石灰。这样可以防止“换杂”发潮,直到吃到来年开“秧田门”也不变质。
过年时,来人来客了就装上几盘这样的土“换杂”,招待客人。客人走了,母亲还要给客人打发一袋这样的土“换杂”。我们口馋了,就背着母亲去坛缸里偷吃几块。
如今,母亲老了,家里也早就不做不炒“换杂”了。但每当过年时,母亲炒“换杂”的香,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甜在我的梦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