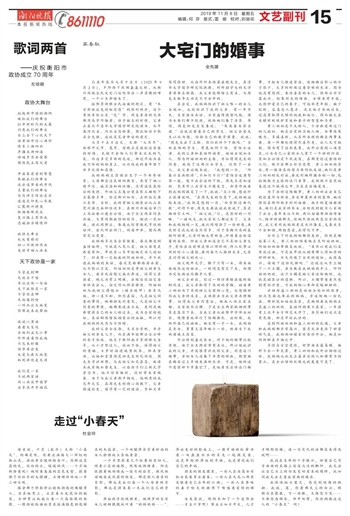乙丑年农历七月十五日(1925年9月2日),夕阳西下炊烟袅袅之时,从衡州府城全氏大宅门后院传出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小生命诞生了。
按照茅洞桥全氏族谱的规定,有“本宗彰继述先德裕宏昌”的排列顺序,这个男孩辈份应是“先”字。同支亲房的兄弟都用马字作偏旁,孩子诞生的时候,父亲正在北平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读书,北平属河北省,河北省简称冀,因此给孩子取名全先骥,这就是笔者命运的前定。
七月十五日这天,又称“七月半”,俗称中元节、鬼节,傍晚正是烧纸送老客的时候,无疑不会给人们带来欢庆的气氛。而这多灾多难的厄运,却过早地压在我可怜的妈妈身上,从而使我的童年留下许多忧伤和遗憾。
我的妈妈王昌韵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养育了她心境平淡、诚实温和的性格,具有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外祖父王夷公曾在彭玉麟帐下当幕僚多年,任过衡州知府,去职后定居江东岸。当时,我的曾祖父翊臣公从山东兖州镇总兵卸任还乡,在衡州府城后宰门上马趾巷兴建全公馆。由于全王两家同在府城,又有同期致仕的经历,相识一见如故,彼此间照应,眷属也经常做礼节性的访问。后代师出同门,同届中举,因而两家交往更密。
我妈妈多次来全家做客,每次都受到盛情接待,可说是人见人爱。祖父母更是疼爱有加,早就在心目中把她定为儿媳妇了。但具有一定权威的何姑奶奶,并不欢迎我妈妈的来访,每次见面都面若冰霜,从不假以言笑。何姑奶奶是曾祖父的亲生女儿,母亲死后随父南北奔波,深得父亲溺爱,视之为掌上明珠,出嫁后还指定房舍供其出入,指定侍从供其驱使。何姑奶奶与我祖父蔚起公(谱名继邓)虽系兄妹,却一直不和,积怨甚深,凡是祖父同意的事情,她都持反对意见;凡是祖父不同意的事情,她都要设法玉成。更何况她希望将自己的女儿嫁过来,成为全家的媳妇,在后嗣保留住翊臣公的血脉,所以对我妈妈的厌恶与日俱增。
我的父亲全述涤,又名全雪帆,并非祖父的亲生儿子,而是满爷继郡公全云峰的长子承祧。他生于衡阳南乡茅洞桥文吉皁,从小才智过人,谈吐不俗,深得祖父的青睐,8岁时接进城里抚养,供其食宿,让他和堂舅周荒初先生同吃同住。周先生学识渊博,与我祖父私交甚笃,故请来我家做私塾先生。以后孩子们上新式学堂念书,他不任家教时,还时常来家做客。由于与我父亲朝夕相处,他俩竟结成忘年之交。在周先生的精心指教下,父亲精通经史,国学有一定的造诣,字和文章写得很好。从海外归来的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执教,对所招学生的文学素质要求颇高。我父亲能够榜上有名,与周先生教导之功是不可分开的。
在全宅,我妈妈结识了祖父唯一的女儿全宛如,也就结识了我的父亲。有一年冬天,王家母女来访,全家盛情挽留吃饭。因为女眷们都不饮酒,就给她们备了清茶。席间,周荒初先生笑着说:“寒夜客来茶当酒。”边说边看着自己的学生。祖父会意先生以此为题,检验自己的教学质量,就说:“周先生出了上联,你们就对个下联吧。”当时在场的学生,有表叔何少伯、堂伯全述潼、我的父亲和表姑何韵甫、姑姑全宛如五人。因为何姑奶奶的主张,并征得周先生的同意,就收了这两位女学生。沉默了一会儿,我父亲站起来说:“我想到一句,‘阳春兴至画配诗’,不知行不行?”堂伯全述潼智商一般,想不出合适的下联,周先生是知道的。见另外三名学生不敢发言,却意外地看到我妈妈微笑了一下,就说:“王小姐,想说什么就请说吧。”在周先生的怂恿下,我妈妈站起来说:“我倒是想到一句,‘白雪飘过曲代歌’,对得不好,周先生要我说我就说了,算是抛砖引玉吧。”祖父说:“行,是很好的一对嘛。”一语双关,把大家伙儿都逗乐了。父亲和我妈相视一笑,彼此间增添了一份好感,再见时交谈也就自然得多。对于青梅竹马的表姐何韵甫,父亲对她也有好感,珍惜着这份温馨的友情。但我父亲知道自己不是祖父亲生子,寄住在这前程是难以预料的,待人处事必须时时小心谨慎,要同每个人搞好关系,尤其是讨得祖父的欢心。
祖父晚年无子,膝下只有一女,将来由谁继承这份祖业,一时间没有定下来,却因为突发病症而撒手人寰。
祖父去世后,经过一场惊涛骇浪般的继嗣风波,我父亲取得了承祧的资格。祖母黄三奶奶为了实现祖父生前的心愿,也想搞好同我父亲的关系,主动提出为我父亲办理婚事。征得我父亲同意后,她派人向王家求婚,王家欣然应聘。于是全王两家联姻的事算是落实下来。当我父亲从旅鄂中学毕业回家,便隆重地举行了结婚典礼。这时候,我的外婆已经病故,她生有一子一女,我妈妈是长女,舅舅王昌年略小一些,继母生下我的满姨王昌鸾。
外公特别喜欢长女,对于她的婚事比较重视。由于全王两家常有来往,所以他认识我的父亲,并且很赏识我的父亲,同意这门婚事,并给女儿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期望她在婚后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他的这个愿望却不幸落空了,是他亲自应许这门婚事,才把女儿推进苦海,使她婚后舒心的日子很少,太多的时候过着苦难的生活。因为他没有想到,秉性善良的女儿,很难应付尔虞我诈、险象环生的场面。女婿虽有才能,也很钟爱自己的妻子,可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容易受人愚弄。况且他才承祧过来,还没有取得足够的权威和地位,因而缺乏在关键时刻保护家庭和妻子的智慧和力量。
黄三奶奶是个大好人,十分疼爱新过门的儿媳妇。她是全家的实权人物,办事很有魄力,多谋善断,从其所办理的婚丧两事来看,每一件都处理得尽善尽美,让人无可挑剔。因为有了这些表象,我外公感到心满意足,以为自己心爱的女儿有了一个好的归宿。需知全公馆是个风波窝,在那里经过磨练的人们,绝不会那么朴实忠厚。黄三奶奶的背后,有一股潜在的势力要伺机发动,她们是黄三奶奶的反对派,要反对她所操办的一切,包括她极力主张的这门亲事。我妈妈不自觉地卷进这个漩涡之中,实在是后悔莫及。
为了办好这场婚事,黄三奶奶让出自己的住屋作为新房,亲自布置新房的装饰。她还将住在衡阳西乡的刘姑娘、南乡的夏姑娘请来,她们是我家的养女,分别找到殷实人家嫁了出去,每年来往不断。两位姑娘帮助招待客人,陪伴新娘聊天,使她尽快地熟悉全家的情况。我父亲对我妈妈更是关怀备至,夫妻关系十分和谐,两相恩爱,浓得化不开。
全府上下对我妈妈都很友好,特别是婚后第二天,黄三奶奶领着她去见何姑奶奶,何姑奶奶面带微笑地说:“虽然以前我们没有谈过话,可是我早就从韵甫那儿得知你的种种好处。今天你做了全家的媳妇,我很高兴,请收下这份礼物吧。”边说边从手上褪下一只玉镯,亲自戴在我妈妈的手上。听何姑奶奶说,这只玉镯是她父亲送给她的,也就是翊臣公的遗物。所以,玉镯带着虽然感到有些凉意,可我妈妈心里却是暖融融的。
庶祖母盛三奶奶是姑姑全宛如的母亲,初次见面也夸我的妈妈,并送给她一份礼品。那时宛如姑姑在家,是她领着我妈妈去见盛三奶奶的。表姑何韵甫不在家,一年前考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了,虽然她们这次没有见面,却是早就认识的。
受到何姑奶奶和盛三奶奶的礼遇,父亲和我妈妈都非常高兴,蜜月生活更添了甜蜜的气氛。我妈妈回娘家时告诉外公,她是如何陶醉在幸福之中。
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易醒。谁料不出一年光景,黄三奶奶和我外公相继过世,我妈妈从此失去最亲近的人和强有力的靠山,在全公馆的处境也就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