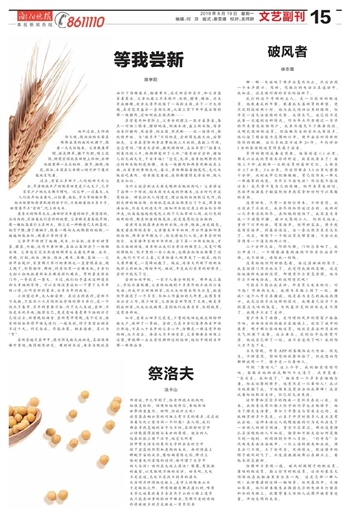端午过后,太阳渐渐火辣,绿油油的禾苗在阵阵滚烫的南风吹拂下,跟着一天天壮起来。父亲戴着草帽,拔光稗草,撒下化肥,喷上农药,稍有空闲就在田埂上徘徊,出神地凝望那一丘丘稻田。拔节,抽穗,扬花,结谷,禾苗在父亲精心的守护下魔术般地变化着。
过去,老家山多田少,人均稻田不足七分,旱涝保收丰产的侧岸田更是少之又少,几乎家家户户的大米都不够吃。记忆中,一过春天,大人们就开始省着吃,以红薯、南瓜、芋头等粗粮补餐,把米饭留给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日夜掰着指头算日子,盼望着早点“尝新”,吃上新大米。
屋东头的侧岸大丘,满田籽实丰盈的稻子,黄澄澄的,沉甸甸的,引诱着我们尝新的欲望。父亲眯笑着卷起旱烟,像一株红高粱伫立在田头,脸上是一种暌违已久的喜悦。他弯下腰,撸了撸袖子,拽着一根向大地鞠躬的稻穗,一遍遍细数谷粒,闻着扑鼻的清香。
父亲早早修理了扳桶、风车、打谷机,母亲补好箩筐、撮箕、竹耙,还用牛粪和稀,在后山渠坝涂了一块晒谷场。父亲选定完全熟透的侧岸大丘最先开镰。放水、割穗、打稻,挑谷、晒谷、扬谷,碾米、筛糠、装坛……父母早出晚归,家里那只乖巧的黄狗也一直紧跟其后,跑上跑下,形影相伴。那时,村里仅有一台碾米机,乡亲们大担小担地挑着新谷去碾房排队碾米,有时甚至排出门外,一等就是一整天。不过,他们似乎喜欢这种漫长却又幸福的等待,可以在闲谈里放松一下累了大半年的心情,打听尝新的置办,分享当年的收成。
小孩望过年,大人盼尝新。在过去的农村,尝新不可或缺,于农历六七月间新谷登场时择日举行,是一个仅次于春节、月半的重要习俗。对于大人来说,尝新,不仅是庆祝丰收,犒劳自己,更是意味着青黄不接的日子已经过去,祈望晚稻满仓。尝新有早有晚,没个定准,谁家的稻谷熟得早谁先进行。一般来说,村子里前后相差不过十天,约定俗成,尽能办置,相互邀请,是以为“节”。
尝新普遍定在中午,因为须先敬天地祖先,菜品便要格外重视,做得颇有讲究。碾好新米后,母亲当晚就在油灯下筛糠簸米,翻看黄历,选定好尝新吉日,和父亲盘算着置办。父亲从墟上买来爆竹、纸钱、檀香、蜡烛。还未等我睡醒,母亲大清早就做了一筛拎豆腐,杀了一只大母鸡,在老瓮里盛出一壶湖之酒,从梁上拿下年中最后留的那一块腊肉,还吩咐我去捉泥鳅……
在堂屋内和堂阶上,父亲分别摆上一张方桌条桌,各点一对烛三根香,摆好碗筷,倒满米酒,盛上新米饭,母亲端来炒腊肉、蒸海蛋、焖豆腐、煎泥鳅……放一挂爆竹,祭祀便开始。与“敬月半”不同的是,尝新得先敬天地,后祭祖先。父亲在堂阶郑重其事地烧三片纸钱,恭敬三作揖,念念有词:“请老天尝新,谢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接着又到屋内烧三片,面朝神龛拜了三拜,“请老祖宗尝新,谢佑儿孙无病无灾,平安幸福!”念完,礼毕,母亲把刚祭祀用过的新米饭倒进狗槽,再夹一块腊肉和两条泥鳅放在上面,让家里的黄狗先吃。每次,黄狗都摇着翘尾巴,先吃米饭后吃鱼肉。母亲微笑着说,连狗都懂得先苦后甜,做人更应如此。
为什么说尝新这天要先喂新米饭给狗吃?父亲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稻米原为天庭的珍珠米,远古时代并没有稻谷。神农担忧人间遭灾,便让他的白狗飘过天河,找到天神的晒谷场。白狗机灵地在谷堆里打了个滚,浑身粘满谷粒,然后又跳进天河,谁知河水把它身上的谷粒全部冲走,仅高高翘起的尾巴上剩下几粒带回人间。我们见到的熟稻穗,都呈倒垂的狗尾状,就是感恩纪念白狗的。
母亲用大铁鼎煮出的新米饭,白净,饱满,油光锃亮,散发着浓郁的清香。父亲请来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邻里的叔伯,照辈分年龄大小,依次请他们入座,分享尝新的快乐。大家请年长的爷爷举杯,尝了第一口新米饭后,才依次端碗动筷。母亲则让我们坐旁边的矮凳上,反复叮嘱别掉饭粒。院子里的一些小屁孩,也跟在叔伯后面围了过来,他们不可以上桌,父亲给每人碗里夹了一把菜,他们又眉开眼笑,一窝蜂地散了。饭后,母亲又用剩下的新米饭拌上新秕谷,喂给牛吃。她说,牛是我们家里的好帮手,尝新不能忘了它。
尝新如同中秋,一家子人要全部到齐。那年我上高三,学校补暑假课,父亲特地跑到十多里外的乡政府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还从大伯借来陈米应急,把尝新节推迟了一个多月。参加工作最初的几年里,我因负责办公室工作,很少回家,父母把尝新节改了又改,硬是等到我回家,从未让我缺席,直到他们远离老家,住到城里,没有再种地。
如今,老家山田多已荒芜,少量的垅田也被流转给种粮大户,改种了一季稻。尝新,已在乡亲们各奔西东中渐行渐远,可在八十来岁的父亲心中,仿佛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从不老去。每逢七月半回老家,父亲都要在田埂上逗留,审视那一丘丘曾经耕种过的稻田,他似乎闻到当年那一阵阵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