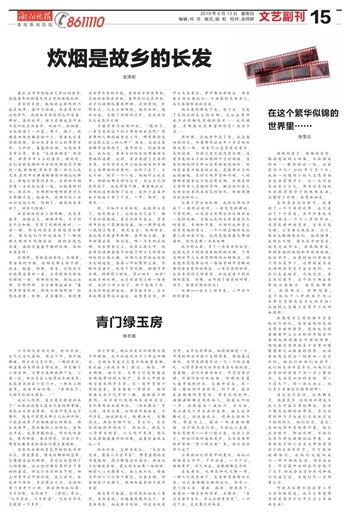六月的天时而炎热,时而凉快,天气也变化莫测。周五下午,西半城骤暗,阴云天边急行军;一跑到东边,倾盆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阳光躲了小会空闲,又劈头盖脸地照下来。小满一过,街边多出三轮摩托车的身影,瓜农老汉停在小区门口,一掀车上的幕布,就地开始吆喝:“卖西瓜了,又甜又红的大西瓜……”
这让人恍惚,莫非夏天提前到来了?如果挑选夏天最具代表性的事物,西瓜必定排名靠前,水果中更是无可替代。想来只有夏天那么火红的烈阳,才能在地里产出相映通红的西瓜。西瓜品类中,有白瓤的三白西瓜,皮肉似冬瓜;也有黄瓤的瓜,外形近哈密瓜,果肉甜蜜,各具特色。但我以为,唯有红瓤青皮的西瓜与夏天最般配。
老农车后厢的青色条纹的瓜并排而立,绿意葱茏,像未经雕琢的翡翠。它圆圆滚滚的模样,更是让我想到了人的肚腩,这让我对西瓜有种出于亲切的喜爱。但这位老汉初来乍到,加上对季节过早的怀疑,我上前问,这瓜保不保熟,老汉滑拉几刀,直接给青门里开个小洞,取出的肉红而厚。不言而喻,瓜熟透了。《诗经》有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吃瓜时令足足提前一个多月。
四千年前,西瓜本是非洲的野生葫芦科植物,也不知道经历多少阴差阳错后,它被培育成炎炎夏日的避暑圣物。徐光启《家政全书》提过: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又有言它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土特产。在传入中国后相当漫长的岁月里,它一度珍贵到只供给皇家,皇家膳食一贯讲究。相传慈禧太后只吃中间一瓤、最甜最沙的果肉;而百姓们发现西瓜通体是宝,食尽果肉后瓜皮勿扔,“西瓜脆衣”可入药,清热消暑,处理掉外层绿皮,可作凉菜,切成丝或片,蘸酱油吃,生脆清淡;西瓜籽晒干后,拿去炒,就是休闲嗑的黑西瓜子。现如今,西瓜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人均可享用,西瓜变成暑期最廉价的水果,盛夏时最低五毛一斤。
西瓜性寒,又称为寒瓜,“天生白虎汤,畏寒人不宜多食”。脾胃虚寒的食用易腹泻,因为解渴清热属性,精壮汉子们偏爱食用。夏天的大地像一块烙饼,晒得人心头攒着火,施工地点处,精疲力尽的工人们停下歇息,打着赤膊,啃食西瓜汁液横飞,现场观看有助于提升食欲。
酒店餐厅装盘,会将西瓜切成三角形,美则美观,但缀着的果肉太少。家里分西瓜,切成弦月形状,啃过后就是月牙,大片也有弊端,切得稍微宽一点,中间的部分牙齿不太够得着。要说最过瘾的,还得是抱着半边一勺一勺地舀着吃。记得学童时代放学后坐在电视机前,盘着腿,边吃边看动画片,尽管没有空调,风扇呼啦呼啦地转,但那就是夏天最幸福的时光。瓜瓤中空后,再一圈一圈地刮外层的肉,刮干净,透出表皮微微的青色后,埋首瓜的底部,满脑满脸都是西瓜味儿,到最后呵地一声,汲取最后一滴红汁。长大后,有次看见十岁左右的表弟,按上述步骤吃完,仿效南瓜头,将西瓜剥两个洞,罩在头上,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孩子的天真行径,不由让人羡慕。西瓜有称号——青门绿玉房,这些小孩子,和他们银铃般的笑声,也住在童年防护罩的“青门绿玉房”里,快乐再简单不过了。
汪曾祺回忆印象中的夏天: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在我看来,吃西瓜和吃火锅一样,一群人吃就更好了。生活毕竟要有仪式感,仪式感唤醒沉睡的记忆。白背心、青门绿玉房、蒲扇、拖鞋、树荫底下,搭建出一幅美好的情景。众围坐,“香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有风”,一口咬下去,真是夏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