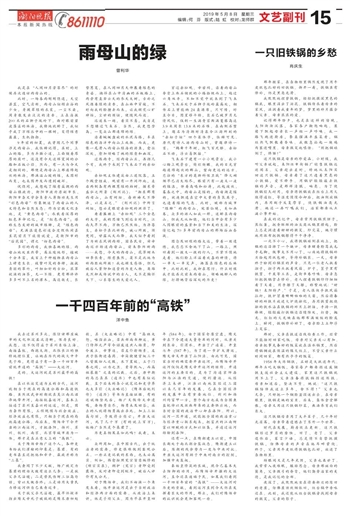那年搬家,在杂物柜里偶然发现了用牛皮纸包扎好的旧铁锅。拆开一看,铁锅虽有修补,仍是黑亮光滑。
我默默地捏紧铁锅,轻轻抚摸深黑色的锅底,眼里涌出了泪花。铁锅传承着母亲的家风,滋润着我童年的梦,梦里的碎片蕴含着父亲、母亲浓浓的爱。
记得那年除夕,也是在这样的傍晚,太阳渐渐沉落,各家各户鞭炮响起。屋檐下飘起母亲长一声短一声呼唤。我一路飞跑进厨房,餐桌摆满丰盛菜肴,锅灶热气飘散着香味。我猴急拈起一块鸡肉塞进嘴里。母亲微笑地嗔怪:“别把锅碰倒了,馋猫!”
这只铁锅是母亲的珍爱品。小时候,我听父亲说起,耒阳灶市街锅厂销售铁锅远近闻名。父亲趁出差时,特地从耒阳买回这只铁锅。母亲看了这只透着黑亮的小铁锅,爱不释手。用锅铲轻轻敲击铁锅的声音,是那样清脆、响亮。为了使铁锅经久耐用,母亲将铁锅放在灶台上用火烧得通红,等温度慢慢冷却后,把油倒放锅内,再用刷子反复摩挲,使铁锅油亮光滑。她还一再叮嘱我们,治家都要从点滴小事开始。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常用铁锅煎饼子,蒸红薯,把香酥酥的油豆腐从锅里捞起,脸上总是润透着甜甜的微笑。炒完菜,她习惯地用抹布把铁锅擦得干干净净。
一次不小心,我将铁锅碰倒在地上,把锅的边沿摔了一个缺口。母亲绷着脸骂我毛手毛脚,做事太不用心了,心痛地将铁锅碎片拾起用纸包好,等待补锅匠。一天,母亲终于盼到补锅匠的声音。只见一位老人挑着担子,担子两头挑着风箱、炉子,筐子里有铁剪、干炭等工具,走街串巷呼唤。母亲急忙把铁锅拿去修补。老人捏着铁锅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用手擦了又擦,称赞地说:“好锅!耒阳特产。”于是,老人很快手执风箱拉杆,铁炉冒着噼噼啪啪的火苗,然后将备好的碎铁片放进火炉烧融化,再用铁剪把烧融的铁水沾在铁锅的碎片上拼接,手持一铁棒槌,轻轻敲打铁锅边沿缝隙处,打磨,拋光。红红的火光映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庞上。瞬间,铁锅修补好了,母亲脸上立即浮上笑容。
那时,父亲在铁道沿线检查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回家吃饭。母亲对父亲关心有加。母亲把事先备好的饭菜放在温水锅里,然后将锅搁放在保温的煤火灶上,不管父亲什么时间回家,都有热乎乎的饭菜。
1958年大炼钢铁,正好是大跃进年代。那年头吃大锅饭,每家每户都要捐送废钢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家里这只铁锅就用不上了,父亲准备将铁锅捐送炼铁。母亲知道后,坚决不肯。她说:“这只铁锅陪伴我这么多年,舍不得!”父亲也无奈,只好把一个铜脸盆捐送出去。在母亲眼里,铁锅是她的宝贝。后来,集体食堂解散,母亲又用这只铁锅炒菜,熬汤养育我们长大。
这只铁锅母亲用了大半辈子。几十年时光荏苒,母亲带着遗憾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时代在发展,厨房炊具更新。这只铁锅经过岁月的磨蚀,旧了、老了。父亲退休后,寡言少语,总是情不自禁抚摸铁锅,仿佛母亲的声音在他耳畔萦绕。终于,父亲用牛皮纸将铁锅包扎好,放进了杂物柜里。
转眼间又是几年光阴,父亲也离世了。我常常入夜难眠,辗转思念。母亲那斑白的鬓角,父亲微弓的脊背,他们勤劳治家的美德,是我记忆的全部。
夜深了,我默默地坐在将要拆迁的陈旧的老屋,仿佛屋顶炊烟依旧,灶台锅中香味还在。此刻,我还能从灶台铁锅旁找到母亲的微笑,父亲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