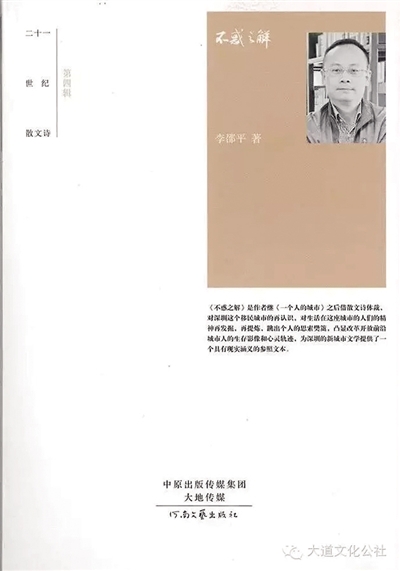邵平对散文诗写作情有独钟,像一只勤劳的土拨鼠,不分日夜忘我地、孤独地挖掘着一条诗的隧道,与时空竞赛。也许,这条隧道一生也难以打通,但并不影响他的行动和坚持。拨动着,就有希望;拨动着,就有未来。“来自乡村的兄弟们,将这个可爱的想法延伸。他们一头扎进填海区……像一群悄无声息的土拨鼠,缓缓打通时间隧道。”(《开往春天的地铁》)和所有的南漂者一样,尽管邵平已有了公务员身份和诗人头衔,但他仍然与普通的农民工兄弟一道,融入了这一神奇的土拨鼠行列。《不惑之解》无疑是邵平人生道路中的一个站点,一个新的起点。诗人以执著的热情实践着散文诗创作的高标准——文字的“轻”、阅读的“醒”、生活的“悟”、思想的“沉”。笔者试分析如下:
文字的“轻”。可理解为诗语言的流畅,生活化描写,用词造句的轻盈自如,恰到好处。记得读邵平第一本散文诗集《一个人的城市》时,我写过一篇《反弹琵琶的流浪歌手》的文章,希望邵平散文诗某些篇章意像的密集度可略微降低,以增强流动性与透明度。读这本诗集,有了新的收获——“那个一心想去流浪的少年,斜挎在铁杆上,面露彷徨。有点痞,有点痞,有点儿怜爱的味道。他耸着双肩,发出口哨。绿色的书包甩开胳膊,较量爬坡的汽车。”(《十七》)这些场景似曾相识,仿佛我十七岁时有过的遭遇,有点痞,有点无奈,有点忧伤,又有点兴奋。因为经历过,又从诗意中寻找回来。生活化的语言,少年时的场景,让人好生喜欢。
阅读的“醒”。好的散文诗像一道闪电,惊醒昏昏欲睡的读者。“糜醉的跑车晃出酒吧,刮碰路边假寐的的士。尖锐声划伤街道。车轮并没有降低频率,蒙头撞向黑夜,碾轧左肩胛的落枕。”(《杂夜偶思》)看看,散文诗也可以现场直播一次酒驾事故。而这一幕只是铺垫,诗人所期望的是——“世界不属于城市背后的任何一块石头:它是你的,我的,一句低吟的,一次仰望或转身的,一片悠然而辽远的。”没有酒驾,就没有伤害,即使在黑夜里,诗人也要张着明炯炯的亮眼,为世界预言。《硇洲灯塔》则直接提示——“对于灯塔,生存的内核在于,谁是后来者永远成谜。”这种不可预知的结局,对于诗人和读者,都是一种期待和向往,一种渴望和刺激,一种再创造的可能,因而也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生活的“悟”。即是散文诗的哲理思考,或曰哲思美;是作者的灵感花开,诗歌与读者共呜产生的美学觉悟。这样的篇章当然俯拾皆是了,如《身上铁》:“流动的铁元素,跟随锄头移居城市,黏合成眼前油亮而高大的塑机。沉默是最好的室友。你也是机器,或是被机器操控的人。”锄头来到城市,难有用武之地,要么变成机器的一部分,要么无声地消失,现代文明如此“强悍”,你奈它何?如《爱莲说》:“世人漠然的荷池,竟是一个人毕生的西湖!”周敦颐和曾国藩同样被书院的清香所诱惑,同样成为书院的痴迷者、崇拜者和受益者。如《枕下书》:“年少时逞强的谎言,叛逆性逃避,真相至今藏在枕头下面。孩子,等你开启灯为谁捂盖被褥——渍黄的纸条折得方方正正,翻过来就是人生的书签。”明白事理,总要经过无数时光的积淀呵。
思想的“沉”。通俗地说,就是诗歌有正能量有思想性,诗人的忧患意识较强。如《岳屏山》:“我想读出危耸的白塔下,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的名字。衡阳。小盆地。四处守卫百米高的小山,像一座座密封的碉堡。七十年前的傍晚,两个士兵钻了进去,抬头示意战友砌死顶盖。”这是大战爆发前的一个片断,从容而不可预知。抗战胜利后,在岳屏山山顶建有“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创造了抗战中以少对多的经典城市防御战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诗人“三十七岁。孑然拾级而上,在抗战纪念碑下,念叨他们的名字。”
邵平以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不懈地挖掘着时间的隧道。乡愁着、爱情着、回忆着、意象着,活得有滋有味,写得风生水起,让人羡慕、让人嫉妒。作为老乡,当然为他高兴。邵平的这本诗集中,还延续了他之前就有的散文诗小说写法,如《殇》《筒子楼里的旧时光》《人生不相见》等,有很浓的诗与小说的意味。此外,邵平的叙事性写法也值得称道,既亲切自然又恰到好处。其生活气息浓郁、人间烟火旺盛、诗意流露自然,适合于不同层次的读者悦读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