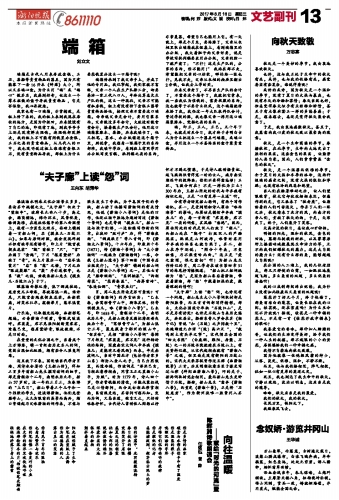瞰蒸湘曲影双清,流下洞庭秋远。危岩突兀玉峰寒,界破苍流一线。谁许见,只鲛宫金绳夜拥鱼龙宴。画船歌扇,对笑水江华。窥楼晕月,惹尽流霞片。
行乐地,记取韶光迅转,画船彩笔题遍。云杳潇湘千顷碧,瞥眼武陵溪畔。君莫羡,君不见渔阳挝断霓裳宴,沧桑已变,想眉黛娇青, 眼波凝绿, 不是旧时面。
在堂堂的文化公园之中,当着成千上万游客,镌一首纪念历史名人的词,竟然出现如此纰漏,颇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这且放下不表。因近读当代学者肖培、周诗永合著的《王船山传》,得知三百多年前船山先生撰写该词的细节。那是清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船山37岁时。这一年的三月三,为春游的“上已日”,船山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姓欧的学生,进城游潇湘。他们先登雁峰山,大儿为眼前的美景而高兴,顺口背诵起乃父咏潇湘的词作来,不意与欧生发生了争执。为平息孩子们的争执,船山讲了他撰写潇湘词的有关情况,他说《潇湘小八景词》是他的旧作,他还以湘中胜地为题材写过《潇湘十景词》也是寄调“摸鱼儿”。船山一边与孩子们游,一边酝酿写作新的词章。出城回“败叶庐”后,得“潇湘夜雨”、“洞庭秋月”等八首词,即《潇湘大八景词》。十六年后,即康熙十年(1671),将《潇湘十景词》与“大小潇湘词”一起编为《潇湘怨词》一卷,今载《王船山遗书》第十四册(中国书店出版发行)。“夫子廊”镌刻的船山词正是《潇湘小八景词》之一。其他七首是“雁峰烟雨”、“东洲桃浪”、“西湖荷花”、“花药春溪”、“岳屏雪岭”、“朱陵仙洞”、“青草鱼灯”。
肖、周二先生所论是否可靠呢?可由《潇湘怨词》的序言证实:“乙未春,余寓形晋宁山中,聊取其体,仍寄调摸鱼儿,咏《潇湘小八景》”。乙未年,即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是船山投身反满抗清运动失败后十年,“寓形晋宁山”,为船山流亡三年,最先藏身于郴州的深山中,“仿其体”,是指“潇湘小八景词”每阕下片都是“君莫羡,君不见”这种转折性的结构,因袭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而来。辛是南渡词人,当时中国北方(包括作者家乡山东)都沦入金人之手,自己力图恢复,而遭冷遇,作该词是“淳熙已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时为1179年,诗人四十岁,作者管钱粮的漕使,不能戎装征战已是心情郁闷,而今反由湖北移官湖南,离前线更远,其苦闷可想而知。发而为词,又忌当道,欲言又止,只好借咏春抒怀。古代诗人常借佳人闺怨以抒怀才不遇之愤懑,于是诗人就借杨贵妃、赵飞燕两位曾得宠一时的女人,痛斥南宋朝廷中的投降派:你们不要得意忘形!玉环、飞燕今何在?不是一样化为尘土?500年后,王船山所处的时代与辛弃疾有相似之处,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今有学者研究船山怨词,有两个写作动机。其一,是受到明初诗人瞿佑“咏西湖景”的影响,而瞿佑是模仿辛弃疾“摸鱼儿”的,每一首都有“君莫舞,君不见”一类的词意,其风格“凄绝”。然而,瞿佑所处的时代是汉人打败了“胡人”,而船山处在“鞑子”打败汉人的严酷现实。既然是山河破碎,咏景时采用辛弃疾的体系也就自然了。其二,船山在序中还说:“阅今十年矣,不竞初意,乃不敢重吟此曲。”这正是“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啊!为船山先生作传记的肖、周二学者在该书第四章51节的结尾抒写慷慨道:“船山把三组词统称为‘怨’。是因为船山眷恋着潇湘,挚爱着潇湘,那‘怨’中藏着炽热的爱,藏着深刻的情啊!
“夫子廊”上读“怨”词,也许还有一个问题,船山先生大小八景词取材都是衡阳胜景,而且首首词都写得精彩。那么,文化公园设计单挑“石鼓江山”,是不是另有讲究?也许是石鼓山自来历史悠久,典故层出。据称东晋人罗会在其《湘中记》曾说“扣(石鼓)之声闻数十里”,北魏郦道元亦谓“(鼓)高六尺“,“数鸣则土有兵革之事”。宋代闻名全国的“四大书院”(白鹿洞、雎阳、岳麓、石鼓)之一的石鼓书院就建在石鼓山上。有关资料记载,从宋代起湖南就有“潇湘八景”之说,但里面是没有衡阳的石鼓山的。宋代大文豪苏轼曾作过五律《画潇湘晚景》三首。后至明朝抗清名臣于谦更写过七律《辟间画潇湘八景》,巧的是于、船两词取材完全相同。兼而船山先生更钟情于石鼓。据称,船山先生“意弃《潇湘八景》,而重定《潇湘十景》,正是将‘石鼓危岩’,作为衡州城唯一胜景列入其中”。
王向东 胡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