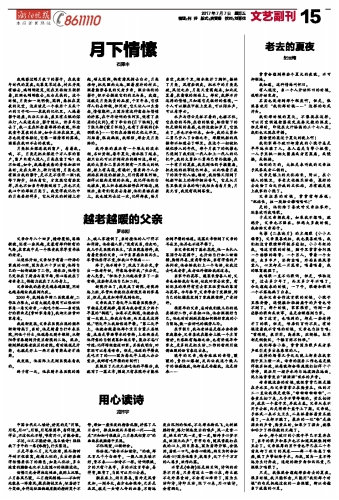我知道,这种情结叫怀旧。
有人说过,当一个人开始怀旧的时候,说明开始变老。
其实也没老到那个程度啊,但是,依然喜欢用“我们那时候……”这样的句式开头。
我们那时候的夏天,不像现在这样,可以用空调遥控器设定成春天般的温度。但是那时,即便在大汗淋漓的三十七八度,我们也比现在幸福。
最盼望的莫过于夏天的晚上啊!
我们家那个破旧却清爽的小院子总是早早地坐满了人。来人总是自带小板凳,一人手里执一柄大蒲扇或者芭蕉扇,或慢摇,或轻拍。
他们的目的,大抵是来听我的父亲拉手风琴或者二胡的。
父亲是镇上的文化站长,所以,在小镇人的眼里,享受文化娱乐活动,最好的去处除了白天开放的文化站,再有就是晚上我家的小院了。
父亲拉琴的时候,常常有邻居说:“纪站长,拉一段给云梅唱唱吧!”
是的,他们除了喜欢听父亲拉琴外,还喜欢听我唱歌。
于是父亲朝我看。如果我不想唱,就跑开,父亲也不强求。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会给父亲面子。
电影《二泉映月》的主题歌《小小无锡景》,父亲最喜欢拉,我也最喜欢唱。我们把这首歌演绎得极其悲切。小小年纪的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常常会闪现一个凄惨的场景: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女孩,走乡串户,沿街卖唱,外面虽然风景宜人,心里却是一片荒凉。唱着唱着,我的眼窝就湿了。
我唱歌一直不记歌词,但是,唯独这首,过去多少年了,而且多少年不唱了,今天想起来的时候,一下子,歌谱和歌词一个不落地跳了出来。
我和父亲合作这首歌的时候,小院子里很安静,连慢摇和轻拍扇子的声音也听不到了。那个时候,家家很穷,听到一些悲惨的歌曲或故事,总是会联想到自家。
除了这首,也唱别的。都是一些老掉牙了的歌,但是,邻居们百听不厌。有时候逢着我不肯唱的时候,父亲也自拉自唱:“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我们那条小巷,常常因为歌声或者琴声吸引更多出来乘凉的人。
这样的场景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在我家院子里上演一次。母亲的服务工作也总是做得极其细致,她每晚都会将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用一桶井水均匀地泼洒在地面,泥土地常常发出“滋滋滋”吸水的声音。
母亲做这些的时候,晚饭常常已经是憋在井水里,而父亲常常正在腌黄瓜。他的刀工一直让我很是钦佩,“啪啪啪啪啪啪”,一条黄瓜切下来,几乎不带停顿的。黄瓜切好后,放在一个盆子里,再放点盐。父亲从来不用手去抓,而是将那个盆子上下颠。父亲说,手抓式一来不太卫生,二来抓着抓着黄瓜就蔫了,一点都不脆了。最后的一记“啪”是拍蒜头的声音,腌黄瓜时,如果少了蒜头,就像咖啡少了伴侣般的无趣了。
如今,那个破旧的小院子早已不复存在了,当年的歌声和琴声也不知随风飘散到哪里去了。父亲浓厚的男中音也早已在二十年前失却了往日的风采——那一年他患了喉癌,做了声带切除手术。而我,因为一直不停地为生计奔波,追赶的脚步匆忙而沉重,已经很少唱歌了。
只是,我依然会想起那些老去的夏夜。很多时候,我只能怀念,只能用“我们那个时候”的句式挑起过往的一些温暖,聊以安慰当下疲惫的心灵。
纪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