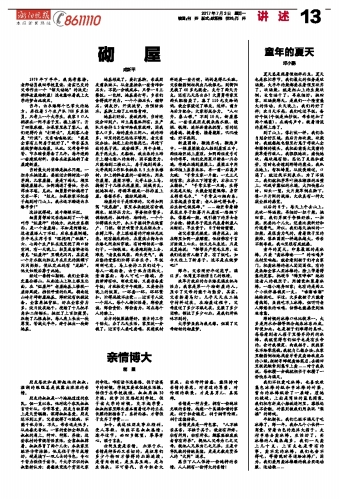1979年下半年,我高考落榜,老师动员我回学校复读,老实巴交的父母作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拆掉老屋砌新屋!这也意味着我上大学的梦由此破灭。
当年,白衣港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居住着5个生产队700多名社员,只考上一个大学生。我家9口人拥挤在一间半房子里,楼上楼下,开了四张床铺。如果家里来了客人,我们还得外出“打游击”。见到客人老是“外流”,父亲喃喃地说:“要是全家有三间房子就好了。”母亲甚至连做梦都在砌屋。从此,父母含辛茹苦、节衣缩食筹备了几年,每年进购一些建筑材料,准备在老基地拆了老屋建新屋。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挑水问题。一担井水挑进屋,要经过古樟树边一排茅厕,几家屋檐。要是下雨天,桶里滴进屋檐水,如同滴进了酱油,井水浑浊不堪。见此,细舅舅许松槐将了父亲一军:“姐夫,如果你家不把房子起到对门山上,我永远不踏进白衣港半步!”
这话说得硬,连牛都踩不烂。
细舅舅帮助父亲选址到了一个被叫作“烂屋坪”的地方。此处坐东朝西,是一个老屋场,不知是何缘故,这老屋场人丁不旺,后来房屋倒塌。当年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六、七两个生产队在这里挖了两口防空洞。有一天晚上,社员成吉聊老远看见“烂屋坪”里磷光闪闪,其实是一个开水瓶内胆瓦片在月光的照耀下闪闪烁烁,便认定此处有“龙脉”,他夫妇殁后葬于此地。
经过一番精心勘测,我们全家决定愚公移山,从南边山上取土移至北面,在“烂屋坪”老屋地基上修筑一座防风堤,挡住呼啸的北风,朝南边山岭开辟新屋地基。那时没有机械设备,全靠肩挑背驮。好在全家劳力多,没日没夜地干,挖断了十几把羊角和二指锄头,挑烂了上百担箢箕,压断了几根扁担,每人肩上长出一块厚茧,苦战大半年,终于挑出一块新地基。
地基形成了,要打基脚。亲戚朋友前来助工,从老屋抬来一些青砖和石头,不花一分钱成本,只管一日三餐饭,一包烟。地基要打牢,乡亲们舍得流汗买力,一个个抬石头,铺卵石,调灰沙,汗流浃背。为预防洪水,基脚上砌了三四路青砖。
地基打好后,要放泥砖。当时还没分田到户,田土属集体所有,生产队只安排0.3亩田给我家放砖。因我家人口多,砌的屋为三间八,放的砖多,田里的泥巴远远不够用。老父亲没办法,挑完上面的熟泥巴,再挖下面的底子泥,放些稻草,用牛去踩。底子泥太生,无黏性,放出来的土砖开上横七竖八的丝拆,因不能受力,只能砌到二楼以上。房子起到两层,大哥找到工作队长批来0.5立方米彬树,加上拆掉老屋的一些树木,用来作屋梁。屋梁不够,大哥土法上马,捣制了十几根水泥屋梁。没钱买瓦,就地取材,将稻草铺成一排排盖上屋,整整齐齐,能防风避雨。
砌屋的日子是艰难的,父母如同驾“没底船”。家里本来就没有余钱剩米,经济压力大,事务相当繁多,调砌泥的、挑砖的、砌砖的,一个个忙得满头大汗。木工手握利斧在做窗户、门框,锯匠咬紧牙关在锯木方,赤膊上阵,身上滚动着的汗珠油光泛亮,还有搞采购的,在霞流古街与白衣港之间来回穿梭,有时哪怕买一根钉子,一捆铁丝,也要跑到街上去,难免“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搞后勤的堂客们忙得不亦乐乎,早饭刚刚吃完,马上安排工匠们过午,每人一碗面条。由于体力消耗大,清汤寡面,每人可吃一海碗,居然津津有味。刚收完场,又要准备煮午饭;才收拾完中午碗筷,又要安排晚上的饭菜。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忙得屁股不沾凳……近百号人没一个闲人,每个人都忙活着。那份虔诚、那份责任、那份卖力,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后方的饭菜搞得好,前方的工作干劲大。办了几天生活,家里没一分钱了,近百号人要吃要喝,买建筑材料还要一些开销。妈妈急得几头跳,父亲翻箱倒柜找出几块银元,到衡阳兑换了40多元现金,支付了两天开支,还有几天怎么办?大舅舅将家里两头肥猪卖了,凑了110元交给妈妈,使全家渡过了难关。这样,前方与后方配合,大家形成合力。“人心齐,泰山移。”不到10天,新屋落成。一些亲戚朋友提来热水瓶、镜框、铁桶、连环画前来祝贺,有的还抱着鸡,提着蛋,搂着蔬菜,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新屋圆垛,鞭炮齐鸣,鞭炮声中,一根屋梁被众人抬到屋顶正中,两位砌匠站上屋顶,如同两位发号司令的将军。他们先用菜刀斩杀一只公鸡,将鸡血滴到屋梁上,屋梁正中用红布捆上盐茶米谷,再一前一后高声大喊:“手拿主家一片绫,一丈三尺还有零;左拴三下增富贵,右拴三下点翰林。”“手拿主家一只鸡,生得头高尾又低;头戴金冠霞佩锦,身穿五彩羽毛衣。”“手拿点心抛向东,主家起屋当富翁;老人拾吃得长寿,后生拾吃做英雄。”……砌匠拿着糖果花生枣子红薯片从屋顶一路抛下来,像落雨一般,吸引楼下的男女老少去抢,糖果枣子花生代表着新屋人兴财旺,早生贵子,日子甜甜蜜蜜。
老父亲容光焕发,满身泥点,站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塑。他仿佛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又无从表达,只是反复地说:“搭帮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这些穷人翻了身,有了饭吃,如今又住上了新房子,这不是在做梦吧!”
那年,父亲刚好年过花甲,满61岁,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改革开放后的白衣港充满生机与活力,我家是第一个砌新屋的人,显示了父母的能干与勤劳。其实,父亲拎着马灯,几乎天天在工地守材料过夜。在砌屋过程中,父母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克服了多少困难,倾注了多少心血,是我们所体味不到的。
大学梦虽然与我无缘,但圆了父母甜甜的砌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