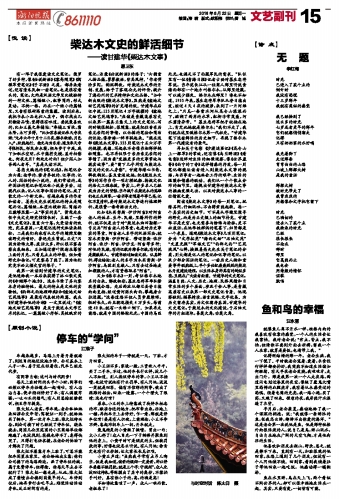易卫东
有一阵子我很爱读文史笔记,搜罗了好多种,像《世说新语》《容斋随笔》《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之类,都弄来看过,还有清末民初一些笔记,也是很有看头的。笔记,大约是汉语文学里比较独特的一种文体,篇幅短小,叙事简约,形式灵动,不拘一格,而在一个短小的篇幅里,又含有很耐思索的意蕴。读到后来,我把书札小品也归入其中,偶尔找出几则翻读品啧,觉得很有味道。要说最喜欢的,比如王羲之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比如苏东坡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真是久读不厌。
姜亮夫编选的《笔记选》,把笔记分为六类:论学的、修身养性的、记事的、记人的、闲话的和小说的。我们常读的,或许闲话的笔记和笔记体小说要多些。近现代以来,记人记事和闲话的笔记,成了散文的一个新文体,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姜亮夫先生说笔记的特点是随笔而记,篇幅短,本质比较松闲,简练而且能够显露一点“事实的真”。萧乾先生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时,主编了一套《文史笔记》,皇皇六十卷,大受读者的欢迎。究其原因,一是笔记这种文体读来轻松,二是我们向来有从文字的缝隙里翻读野史的嗜好。鲁迅先生曾说,正史“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我第一次读到甘建华的文史笔记,是他送给我一本后来获得了冰心散文奖的《冷湖那个地方》。这本书除了其内容本身的独特性,最大的特点是文体的实验性。《西部之西地理辞典》和《盆地文坛艺苑逸事》是最有代表性的两篇。我在《甘建华和他的冷湖》一文里说过:“《盆地文坛艺苑逸事》是关于柴达木文学艺术的札记。一篇篇短小抒怀、灵性跌宕的笔记,沿袭《世说新语》的路子:‘六朝重人物品藻,寥寥数语,皆具风神。’作者博洽多闻,钩沉辑佚,对柴达木文学的开创、发展,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提升了海西州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品格。”如今新出版的《柴达木文事》,显然是《盆地文坛艺苑逸事》的扩充增补版。甘建华在后记中说,123则笔记4万字规模的《盆地文坛艺苑逸事》,“应该是青藏高原有史以来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史笔记,写的时候很轻松,很随意,就是把往昔亲历亲见亲闻的事情,以白描的笔法和简洁的议论,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现在这部《柴达木文事》,333则笔记十五六万字的规模,我想,写起来不会像当初那样轻松随意,也不再仅限于亲历亲见亲闻的事情了,因为要“发掘更多的文事掌故与现实故事”,要“留下几乎所有与柴达木有关的文化人身影”。甘建华潜心书斋,辑佚钩沉,甚至重返故地,把《柴达木文事》的写作当作一项打捞沉船、抢救文化的浩大工程来做。事实上,许多名人已经成为历史的背影,当年战斗在柴达木的英雄们也正在凋零,一些当事者随着年事已高,记忆不复清晰,要对柴达木文事进行梳理辨析,是很费一番考据功夫的。
比如《木买努斯·伊沙阿吉》对阿吉老人的姓名、生年、民族、里籍所作的辨析,就不仅是出于对“柴达木油田勘探一号尖兵”阿吉老人的尊重,也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阿吉老人名字的汉语写法,就有木买努斯·伊沙阿吉、穆迈努斯·依沙阿吉、依沙·阿吉、伊沙克·阿吉等多种;对他的民族,有的记载为维吾尔族,有的说是藏族牧人。甘建华经过细读文献,认真辨析,得出结论:老人的名字为木买努斯·伊沙阿吉,乌孜别克族人,只有去过圣地麦加朝觐的人,才有资格取名“阿吉”。
又如《格尔木》一则,考证格尔木地名的由来。解放初期,慕生忠将军率队修筑青藏公路,先后两次从都兰县香日德向南直插,经过黄河源头向西,攀越唐古拉进藏,“这条道路不但人员步履维艰,耗时长久,而且驼运损失4万多头,每前进40米,就有一头牲口倒下。如果再走前路,就是中国的骆驼死光,中国的马匹死光,也满足不了西藏军民的需求。”队伍里有一位《青海日报》记者古洪对慕生忠将军说,当年范长江从一位商人那里听说青海西部有一个地方叫格尔木,从那里进藏,可以减少损失。格尔木在哪里?谁也不知道。1953年底,慕生忠将军率队从香日德出发,经过4天4夜的跋涉,来到了一片河滩之上,“只见一条雪水河从昆仑山滚滚而下,滋润了两岸的水草,红柳非常茂盛,河水碧清异常。”慕生忠将军把手杖插在地上,肯定此地就是格尔木:“我们不走了,我们就在这里做格尔木第一代祖先。”甘建华笔下这些鲜活的历史细节,再现了格尔木第一代建设者的豪气。
再如关于电影《沙漠追匪记》《昆仑山上一棵草》的掌故,还有像《乌兰醉酒》《看电影》这样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像《世界屋脊》《西宁的丁香》这样情感的抒发,每一则笔记都能让读者进入到柴达木文事的现场,与当事者一起体会工作的艰辛、生活的温暖和情感的跃动。我们从一个个散点分布的细节里,透视出甘建华对柴达木文事的掘幽发微之功,以及对柴达木人事的一往情深之爱。
阅读《柴达木文事》的每一则笔记,沉潜其间,仔细玩味,不由得肃然起敬。每一个真实的历史细节,可不是从字缝里搜寻的野史,而是为正史缀上的细节补充。甘建华不是史官,也无需参与粉饰与涂抹,更不必废话,在他率性挥洒的笔墨下,归旨都是一个求真。通观《柴达木文事》几百则笔记,分为“文学拓荒”“海西文坛”“石油文苑”“文星光照”“军旅文艺”“西部之西”“艺苑流风”七辑,按照姜亮夫先生关于笔记的分类,则大都是记人的笔记和记事的笔记,以及少部分闲话的笔记。一些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跃然纸上,半个多世纪轰轰烈烈的柴达木开发建设进程,以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绚烂多姿,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甘建华的文史笔记,涵盖自然、人文、历史、地理、民俗风情和日常生活的多个层面,涉及千余人事,是青藏高原有史以来第一部文史笔记专著。他观察独到,描摹精准,语言流畅,文字优美。为历史留存真实,为文化留存基因,甘建华的文史笔记,于柴达木的文化建设,于石油文学的开拓进取,善莫大焉,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