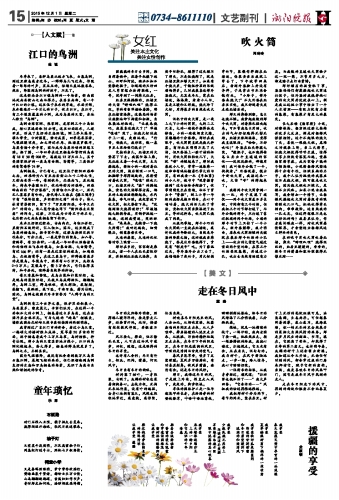关注女性创作
吹火筒
肖玲玲
湿漉漉的冬日去乡间,独自撑着雨伞,摁着手机摄下远山、田野和河流,雨水不知不觉渗进鞋子,冷飕飕的只好回友人军家想办法烤鞋袜。一寻,就寻到了一间柴火灶房。
灶房里热腾腾的,灶塘里的火苗“噼哩叭哩”烧得正旺。军的母亲邓姨哈着腰,蹲在灶塘前添柴。这熟悉的场景让我倏地卸下拘谨和扭捏,自来熟地对她说:“让我来烧吧,我最喜欢烧火了!”邓姨“噗嗤”笑了,把烧火钳往我手上一递,爽朗地说:“行呀,你烧火,我炒菜,做一桌乡里土菜给你们洗尘!”
交接的当儿,灶塘里的火势萎了下去。我慌忙添上柴,见灶边立着一个吹火筒,立马操起来,将细小的一端对着灶里的火源,然后深吸一口气,把腮帮子撑得鼓鼓的,再将嘴对着吹火筒,“噗噗”猛吹几口,灶塘里的火“轰”的腾起来,黄色的火苗蹿得老高,锅里的土鸡滋滋沸腾起来,水汽袅袅,香气四溢。我赶紧放下吹火筒,把火势控下来。“没想到你火烧得顶好!”邓姨翘起大拇指夸我,用锅铲挑起一块鸡,送到我嘴边,笑眯眯说:“来来来,先犒劳一下烧火师傅!”我叼过鸡块,细嚼慢品,顿觉唇齿生香。
久违的感觉,久违的记忆霎时浮上眼前……
那时在乡村,家家都是柴火灶。若一个人在灶头煮饭炒菜,再转到灶后烧火添柴,自然手忙脚乱,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不是饭烧糊了,就是灶塘里柴不够火灭了。如果有个烧火匠,干做饭炒菜的活就顺畅得多。儿时我最喜欢帮外婆烧火,尤其是冬天,窝在灶塘边,添添柴,看看小人书,真是又暖和又舒服。烧火除了火钳,用得最多的自然是吹火筒。
记忆中的吹火筒,是一截上大下小的竹筒筒,大约二三尺长,大的一端被手握得油光铮亮,小的一端被烟熏火燎,黑魆魆的十分寒碜。那时在我眼中,吹火筒简直就是烧火神器。有时灶里明明不见了火苗,但只要添上一些干枯的松针,用吹火筒轻轻吹几下,火就“嘭”的燃起来了。那时我最迷小人书,常常一边添柴一边津津有味地翻着巴掌大的书页。有回我看一本《半把剪》的小人书,被书中“说曹操曹操到”这句话给弄糊涂了。故事明明发生在清朝,冷不丁冒出个“曹操”,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楞是搞不明白,在心中嘀咕着,烧火的活儿乱了章法,竟把吹火筒当柴添进了灶里。等回过神来,吹火筒已烧成了两截。
从我记事起,那个小巧的吹火筒就一直放在灶塘边,或许比我的年龄还大,自然是外婆的珍爱之物。这回被我当柴烧了,要是让外婆晓得了,肯定有“剥皮亏”吃。为了蒙混过关,等外婆外公出工去了,我悄悄拾了截竹子,用火钳捅穿竹节,装模作样搁在灶塘边。伪装妥当后我就上学去了,下午放学回来后,看到外婆脸上并没有异样,于是拿出书本准备做作业。“小玲子,帮外婆来烧火!”不久外婆在灶房里召唤,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灶塘后面。
那天的柴特别潮,怎么也烧不燃。我拿起我做的那个吹火筒,对着柴禾猛吹起来。可不管我怎么用劲,吹出的气却好似跑得无影无踪。灶塘里浓烟滚滚,熏得我直流眼泪。“哈哈,不好吹吧!”外婆在灶头捧腹大笑,“傻妮子,也不晓得你怎么弄出个直通通的家伙——没阻没挡的,哪能用哟!我叫你外公做了一个,拭拭看。”外婆说着,摸出个新吹火筒。我接过来一吹,火苗“呼”的蹿起来了。
我将两个吹火筒拿到一块一比,终于发现了端倪——两个吹火筒差不多长短,中间都有三个竹结,但我把三个竹节都打通了,而外公做的那个,只打通了靠近粗端的两个竹结,小端的那个竹节上只钻了一个小孔。经外婆解释,我才明白,原来吹火筒助燃的关键就在最后那个竹结的小孔上——吹出的大量空气通过前面两个空竹结,在第三个竹结受阻集聚,再通过小孔,吹出去自然有劲道有力度。而我做的直通吹火筒缺少这一阻一聚,不管用多大力,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那时顽劣的孩童犯了事,婆婆妈妈们都爱操起吹火筒追打孩子,但外婆对我烧掉她心爱的吹火筒并没放在心上。倒是我从这桩小事中悟出了一个人生哲理——有阻力就有力量的集聚,有集聚才有更大的暴发。
长大后读《杨家将》小说,对穆桂英、杨宗保这些大英雄并没多大反应,倒是对杨排风惺惺相惜。这个不起眼的烧火丫头,善使一根烧火棍。危难之时披挂上阵,当上火将军,把烧火棍使得呼呼生威,惊得辽军主帅殷奇落荒而逃,重振杨家将军威,成为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小说将杨排风塑造得十分有个性,但联系她的名字,我个人认为她使的武器应该不是烧火棍,很可能是吹火筒。因为烧火棍吹不燃火,更排不出风嘛。如果小说由我来写,我会增加一个情节,让杨排风操起吹火筒对着殷奇的眼睛猛吹几口气,把他吹得晕头转向,乖乖投降。这自然我的一孔之见,但这样想像不是也挺好玩的吗?我甚至认为,作者或许跟我一样,对吹风筒感情深厚,才会塑造出杨排风这么鲜活的角色。
在回味中用吹火筒吹着灶塘,柴禾“噼哩叭哩”烧得旺旺的,灶房里暖暖的,香香的,将冬日的萧瑟和寒冷驱散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