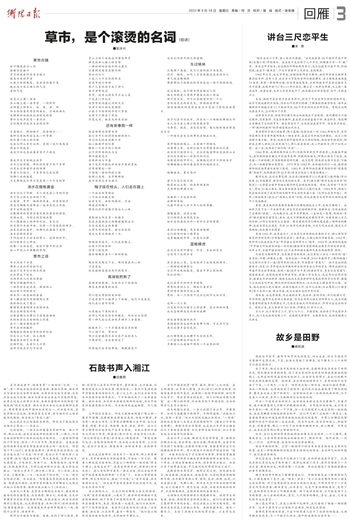■李 昂
“粉笔生涯六十年,童心未泯雪盈颠。”这是我在第38个教师节前夕所写《自题小照》中的两句。我这辈子先后待了几个单位,但都离不开一个“教”字。虽当过中学校长,当过教育科研机构负责人,也当过教育行政干部,但说到底,我是个“教书匠”,平生不曾离开三尺讲台,直到现在。
1962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衡阳县文教科,担任中学语文教研员兼函校专师。是年9月,我去金兰学区给老师们面授课文。金兰镇离县城西渡70来里,虽有一条衡邵公路,但没有始发客车,从衡阳城里开来的过路车又买不到票,我便开动“11”号——步行前往。脚上穿一双笋壳草鞋,头上搭一条湿毛巾。走着走着,毛巾上水分蒸发干了,就在路边水田里浸湿、拧干,又搭在头上。
本来,面授可在区里乃至县里举行,但为了节省老师们的时间和开支,我尽可能送课到片到校,同时也听老师们的课,了解各校的教学情况。每年我都要徒步跑遍全县11个联合学区、84个学区的四五百所学校,有的去过两次甚至多次,总行程不下万里。
这样虽然辛苦,但老师们强烈的求知欲使我十分欣慰。来听课的不只语文教师,还有各科、乃至全体教师,甚至有当地的基层干部、商店职员。面授那天仿佛成了当地的节日。教室里坐不下,大家就站在窗外听。初出茅庐的我,一种“教师的教师”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其间有许多动人的故事,限于篇幅,这里仅说一件:1963年国庆节,长乐学区两位男女青年教师借来一辆吉普车,接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他俩恋爱中遭到男方父母的阻挠,面临分手的危险,刚好我去那儿讲授《孔雀东南飞》,两人深受感动,决心冲破阻力,终于如愿以偿。这一来,我便成了他们的“月老”……
1966年秋,我调到衡阳县六中(今衡阳市新民中学前身),任教高中语文;后任教研组长兼文学社指导老师,仍教两班语文;即便以后当了校长,我还教一个班的课,并为请假的老师代课。我总觉得,脱离讲台便不自在,不踏实,而一进课堂便如鱼得水。1979年至1982年,我和组内同仁一道,赢得原衡阳地区高考语文成绩三连冠。1983年,在衡阳地区教育局组织的“创最佳课”活动中,我执教的《阿Q正传》评为全地区三堂最佳课之一。
教学之余,我还从事笔耕,先后在《湖南教育》《人民教育》《教师报》等刊发表20余篇教育、教学论文及经验文章。其中《语文课“教学生能自读书”的探索》一文荣获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颁发的金奖。同时,我写的“下水作文”,有近20篇以散文、杂文等体裁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1984年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创作的反映中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这里升起》。同年,《湖南教育》杂志以“两栖人李昂”为题,对我在教学与写作两方面的成绩作了长篇报道。
其时,某出版社和某教育类报刊社都想调我去工作,我婉言谢绝了。我始终只乐于当一个业余作者,讲台才是我的终极归宿。感谢讲台,它使我练就了过硬的“招数”。比如教古文,我不用带教材,一支粉笔一张嘴,熟练的“背功”磁石般吸引着学生;再如,我从不照搬现成的教参资料,而着意融入自己的体验,以师之体验促生之感悟。每当看到同学们那水葡萄般心领神会的眼神,我就觉得无比满足。尽管20余年吃的食堂饭,不是几坨油豆腐,便是几只烧辣椒,但我都不觉得苦。
直到1991年,我年逾五十,才结束与老伴两地分居的日子,调入衡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今市教科院前身)。两年后,又调入衡阳市教育局。1992年,衡阳市人民政府授予我“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1994年,我领衔创建的《中学语文听说读写四能一体训练》教改项目荣获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的金奖。次年4月,全国中语会组织25个省市的语文教师代表来雁城观摩、取经。
无论是当教科所长,还是教育局副局长,我总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泡”在学校,听课、评课或上课。这里也说一个故事,2019年教师节,《衡阳晚报》文艺副刊刊登了一篇《恩师李昂》的文章,作者署名“曾高飞”。他不是我的授课弟子,而是20多年前我任市教科所长时祁东县七中的学生。那年我组织全市高中毕业会考阅卷,发现一篇《跬步与千里》的满分作文,考生正是曾高飞。阅卷结束后,我便赶赴考生所在学校,在高三学生会上,先让考生谈写作体会,接着我作详细讲评。随后又把此文及其讲评印发各校供同学们参考。据高飞以后的来信中说,那次讲评对他鼓舞很大,从此他走上课余写作之路。后来,他先后到人民日报社、法制日报社工作,迄今已出版《生如夏花》《小镇青年》等十来部小说、散文作品,成为全国知名的中年作家。
退休后,我没有闲着,仍应邀到全市,包括县、区的学校,举行校园文学、中华诗词、高考作文等项义务讲座。作为全市首位语文学科带头人,我应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多尽绵薄之力,尤其是在语文学科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的今天。退休以来,我义务讲学300余场,听课达50余万人次。
古人云: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不揣冒昧,我的弟子中也有许多贤人,而门生之数则远超三千。我感到无限荣幸。如果有来生,我仍愿栖居三尺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