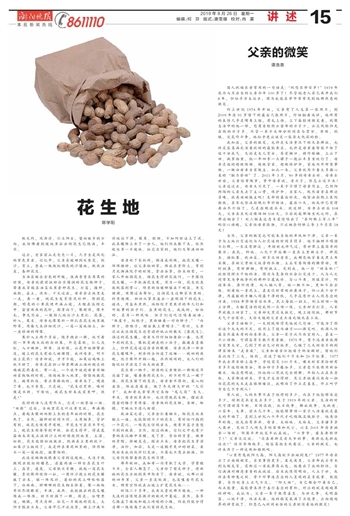秋无约,风渐凉。伫立阳台,望向故乡的方向,我仿佛看到坡地里扯出的花生已饱满,丰实。
过去,老家前山光秃秃一片,几乎全是风化的紫色页岩。记忆中,父亲在坡岰到处垦荒,刨沙,育土,整成一块块红褐色的沙壤地,秋栽油菜,春种花生。
当油菜褪去金色的外帔,挂满青青长角果的时候,母亲就提前挑好壮实圆润的花生做种子,带着我穿梭在油菜丛里套种花生。打窝,播种,施肥,盖土,浇水。十天过后,母亲会去地里走一走,看一看,视花生发芽情况补种。待到花期,明亮的小黄花便开满山坡,点缀在丛绿之中。密密麻麻的花针,躬身向下,像胡须,像牛毛,争先恐后,一股劲儿地往沙土里扎。花落,针入,果生。母亲也像果针一样扎在花生地里拔野草,用柴火灰拌细泥沙,一窝一窝地培土,如一座移动的蹲像。
果针入土两个月后,随手拽出一棵,就可看到一串串鸡头状的白幼果,外壳柔软,仁儿浅红,入口嫩甜,鲜香。这时候,山鼠开始频繁出没,坡上的花生有些儿被糟蹋。我问母亲,何不放上鼠药?母亲却说,万万不能,如果让鸡啄上就不好了。母亲是在担心邻里那满山满岭跑去的鸡被鼠药毒死。有一次,一个放牛娃趁母亲荷锄回家做饭的时候,悄悄地潜入地里,偷偷地拔花生,被哥抓住。哥正要揍他时,母亲来了,喝退了哥,也不责骂,只是说:“花生还冇熟,咯时候是水籽,可惜哒,收花生时来我家里呷,快走!”
农村的活儿没有尽头,总是一桩紧接一桩。“双抢”过后,当地里花生叶泛黄变疏,布满褐点,看起来像奶奶脸上长的老年斑的时候,花生熟了。当然,播种的时间不同、土质相异、管护有别,收花生便有早有晚。早花生可在月半节吃上,晚花生则要等到中秋。扯花生得早,得在晨露尚未蒸发正滋润沙土的时候赶到地里。土湿,松软,花生能轻松地拔出,脱漏在土里的就少。如果沙土板结了,或是种在黄泥田里的,须用锄头一窝一窝地挖,挺费劲的。
我迷迷糊糊地跟着父母到达坡地,天边才微微现出殷红的曙色,清露雨滴一样坠在花生叶上,晶莹,透亮。父母低头弯腰,拢起一窝花生穰,靠近根部使劲一扯,一团怀沙抱土的花生穰拔了出来,猛一阵甩抖,蓬松的泥土哗啦啦落下,白麻麻、胖嘟嘟的花生相互挤着,像一枚枚耳环尽现眼前,丰满,成熟。我把拔出的花生穰堆成一堆堆,时不时摘下一颗,剥壳,往嘴里送,嫩脆,有点清甜。扯完一片坡地的花生,太阳才探出头来,父母早已汗流浃背,额上汗珠不停地往下掉,眼角、脸颊,不知何时沾上了泥。我在穰堆上坐了一会儿,他们仍未歇下来,依然赶往另一片坡地。扯完自家的,他们又帮满奶奶扯。
母亲砍下长杜荆,钩连成荆绳,把花生穰一堆堆捆好,让父亲挑回家,堆放在堂阶上。等到月光洒满院子的时候,拿出谷箩,拎来矮凳,一家人开始摘花生。摘花生得讲究技巧,一手攥住花生穰,一手抓满花生果,用力一转,花生就悉数脱落到掌心。邻里的伯娘婶娘丢下碗筷,煮完猪潲,便围过来帮忙,边摘花生边聊家长里短、村里趣闻。奶奶从箩里盛出一盆刚摘下的花生,搓洗,用盐水煮熟,端给院子里乘凉的爷儿们和听故事的孩子们。盐煮的花生,咸咸的,粉粉的,是另一种风味。孩子们边吃边唱着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着一对白胖子。”“白胖子,挤帐子,醒后戴上黄帽子。”有时,父亲还让我边摘花生边背诵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摘过的花生穰,母亲又仔仔细细查验一番。也有个别的花生,像机灵顽皮的小孩子,躲藏在茎藤上,但终究没逃过母亲的眼睛。母亲洗净一部分花生穰喂牛,剩余的全扔进了池塘……秋初的夜晚,院子像炸开锅一般,热热闹闹的,大人们的愉悦似乎湮没了白天的疲累。
花生甫一晒干,好酒的父亲便抓一颗贴近耳边摇了摇,嚷着要剥花生仁,时不时炸上一碟下酒。剥花生留下的荚壳,母亲舍不得扔,装入蛇皮袋,堆放在柴房,做了冬天烤火炉的“火引子”。我和哥也常常用它来给“甩火筒”生火。年关,母亲就算再忙,也还得做花生酥,摆放在团盒的格子里待客。母亲做的花生酥,香甜,酥脆,可她从不逢人炫耀。
栽油菜之前,父亲会扛着锄头,给花生地再翻上一遍,也能捡到不少的花生。有时恰巧捣到一个鼠穴,一堆花生惊现出来,便有半篮子意想不到的收获。当然,经过雨淋,它们之中也有少量的在沉睡中苏醒,发了芽。雪白的芽茎,嫩黄的芽帽,挤破荚壳,探出头来。母亲把花生芽濯净,油炒,加蒜,又是一道脆牙爽口的好菜。虽然后来我怕伙伴们笑话,不屑也不愿去拾漏,但父母仍保留着捡花生的习惯。
那年秋初,我和哥一同考取了大学。学费缴不齐,全家人都急了。父亲除了留足种子,将新收的花生全挑到蒸市街卖了。母亲说,从那以后的四年里,父亲一直没饮酒,也没嚷着炸花生米,稍有空隙就在山坡上扩宽花生地……
时隔二十多年,我再次靠近那片坡地,一种久违的温情便在微凉的秋风中蔓延。虽然,杂草已掩盖了坡地和坡上崎岖的小路,但我仍能分得清那一块块属于我们家的花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