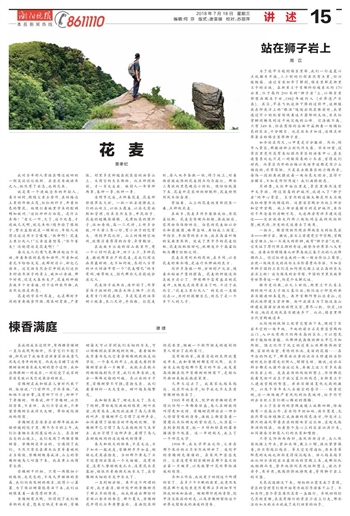我对当年村人常挂在嘴边说叨的一则笑谈记忆犹新。其意是告诫读书之人:纵然有了出息,也别忘本。
说是有一个进城念书的年轻人,某日回村,跟随父亲去劳作。其时路边土里的作物正茂,红红的秆子,开着白色的繁花,他便打着城里学来的腔调明知故问:“这红秆秆打白花,是什么东西?”老父一听,火了,这个死崽,才进城几天啊,就忘本啦?随手捡了根棍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好打。年轻人痛得边逃边用方言嚷嚷:“救命啊!花麦土里打死人!”父亲追着怒骂:“你个畜生!还晓得这是花麦啊!”
每次大人们眉飞色舞讲起这个笑话,伴着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听者和说者无不哈哈大笑。我那时还小,却也已读书,这笑话自然会引申到我们这些乡村读书孩子的身上,被加以告诫。那个时候,还是大集体生产,花麦的种植在故乡十分普遍。对于这种农作物,我自然也很是熟悉。
花麦的学名叫荞麦,也是那时乡间的重要粮食作物。因其耐贫瘠,产量低,村里多是种植在挖垦后的油茶山上。又因它的生长期短,从点种到收割,才一百天左右。故村人一年常种两季,春种一季,秋种一季。
清明节之后,点种春花麦。花麦种拌进草灰火淤,一抓一抓丢进撩成土行的山岭上,以松土覆盖。以后无需施肥和管理,任其自然生长,开花结子。花麦的植株很耀眼,光滑红亮的圆秆子,状如香棍,高一二尺许,上部多分枝,叶片若三角心形,有小孩子的巴掌大。待到开花之时,山上的绿树空地间,就像浮着厚厚的白雪,异常靓丽。
在我故乡往南的深山数里外,有一个小村叫花麦冲,田少土少,多种花麦。据说那里出产的花麦,是我们周边品质最好的。也不知何故,在村人日常的口头词语中有一个“花麦嘴巴”的专有词,略带贬义,指代那些尤其能说会道之人。
花麦结子成熟后,连秆割了,用箩筐筛子挑回村,铺在禾场上晒干。打花麦有专门的花麦棍,多是笔直的油茶树小枝条,长二尺许,手指粗。打花麦时,每人双手各执一棍,蹲于地上,对着面前拢成堆的花麦梢头均匀敲打,那些三角状的黑色硬壳小籽粒,便纷纷脱落下来。花麦秆是农田的好肥料,花麦籽则用风车除杂质。
紧接着,山上的花麦地重新挖垦一番,点种秋花麦。
在故乡,花麦多用手磨推成粉,蒸花麦饺粑。花麦壳坚硬而粗糙,推成粉后,需用粉筛筛除碎壳。白色的花麦粉以冷水和浆揉团,略带盐味,再切成三指宽、中指长、手指厚的长方块,放在高粱秆做的笼屉里蒸熟,就成了黑乎乎的花麦饺粑。花麦饺粑很好吃,软硬度介于高粱饺粑与 子饺粑之间。
花麦具有利水的药效,在乡间,以老花麦籽熬水喝,是治疗水肿病的良方。
同许多杂粮一样,分田到户之后,随着水稻亩产量的提高,花麦的种植逐渐在故乡消亡了。即便那个富有盛名的花麦冲,大概也是徒有其名了吧。不过于我而言,“花麦土里打死人”的笑谈一直铭记在心,并时时提醒自己,别忘了是一个乡下人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