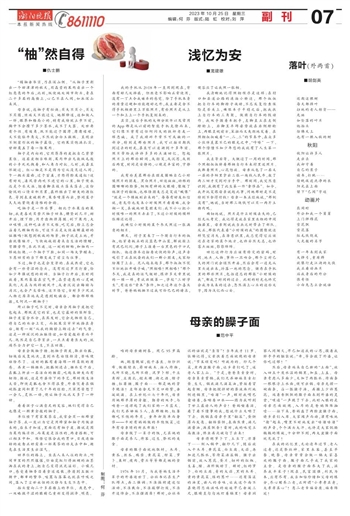■范中平
咱的母亲谢树春,现已95岁高龄。
她,聪慧靓丽,能干善良。纺纱织布、做鞋缝衣、莳田收禾、接人待物,无所不晓,无所不精。泥萝卜榨、干豆角榨、豆腐乳、糯米糟、湖之酒、橙子糖、红薯糖、臊子面……都是她的拿手绝活!左邻右舍无不交口称赞,垂涎欲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母亲用她那单薄的身躯、勤劳的双手,与咱爸一道撑起了我们家的一片蓝天。我们兄弟姊妹5人,在那糠粑、红薯都吃不饱的年月,童年却简单而奢侈——平时有妈妈做的半饱饭菜,过年有母亲缝的新衣布鞋!
母亲做了一辈子的饭,尤其她的臊子面是养儿、待客、过生、祭祀的美食。
母亲的臊子面就地取材,木耳、黄瓜、丝瓜、鸡蛋、黄花菜、榨菜、萝卜、鱼虾、瘦肉、骨头等等都是她的食材。
1976年10月,与我爸妈生活半辈子的外婆逝世了。公社书记在生产队蹲点,再三强调:不准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准戴白,不准敲锣打鼓,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摆酒席!那时,公社书记的话就是“圣旨”!当年我才11岁,依稀记得,父亲扶着悲痛欲绝的母亲说:“节哀顺变吧!听政府的。炒几个菜,煮两盆臊子面,让乡亲们吃了,送老人家上山。”于是,爸爸负责食材,母亲负责掌锅,我们兄弟姊妹负责打蛋、生火。锅底滴几滴菜油,紧接着冒起青烟。母亲把搅拌好的蛋液麻利地倒进锅里,“哧溜”一声,顿时我嘴巴翕动着,吞咽着口水——因为我听到了世上最诱人的声音!爸妈噙着泪,看了看不懂事的我,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铁锅在母亲手里“翻滚”,蛋饼薄而发亮。翻转蛋饼,表面焦黄,滴几滴酱油,满屋飘香!霎时,我的味觉立马激活,馋虫再次被勾了出来!
母亲将胡萝卜丁、土豆丁、凉薯丁……倒入锅中,翻炒几下,随后放入干木耳、黄花菜、白豆腐、大蒜,再加进几瓢水,等待菜汤滚锅。臊子出锅前,放入葱花、蛋片、切碎的红椒、生姜、醋。汤料做好了。顿时,红的萝卜、白的豆腐、青的大蒜、黑的木耳、黄的黄花菜、绿的葱叶……还有荡漾的油星,诱人的香味,让我这个尚不甚晓得悲痛滋味的娃娃早已垂涎三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里!母亲洞察人间烟火,早已知道我的心思,摸着我胖乎乎的脑袋说:“乖,等会敬了外婆,让你吃过够!”
然后,母亲端来自己擀的“土面”,放入四五十度水温的锅里,加盐、上盖。母亲考虑人多面少,又加了两瓢水。待面条一根根浮上水面,便可出锅。母亲先捞一碗面条,舀一瓢臊子汤,再撒上少许葱花,端着香飘飘的臊子面来到外婆的灵堂,“噗通”一声跪了下去。此时入眼的是母亲悲痛欲绝,入耳的是爸妈阵阵抽噎……接下来,爸妈盛了两脸盆臊子面,请乡亲们入席。大家闻声而动,津有味地“抢”起来,嘴里不时地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个个满头大汗。也许是大家饥肠辘辘的缘故,十分钟不到,两大盆臊子面就见底了!
在我的记忆里,无论逢年过节、老人过寿,还是祭灶神、家里来客,甚至早餐、晚餐,母亲常常会做一锅大家喜欢的臊子面。臊子面几乎成了我家的主食。是母亲的臊子面养大了我,滋养我半辈子!现在,民富国强,利民为本,应有尽有。我当加倍珍惜和父母的缘分,尽心赡养二老,正所谓“小孝孝其身,大孝孝其心”!愿二老幸福安康、福寿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