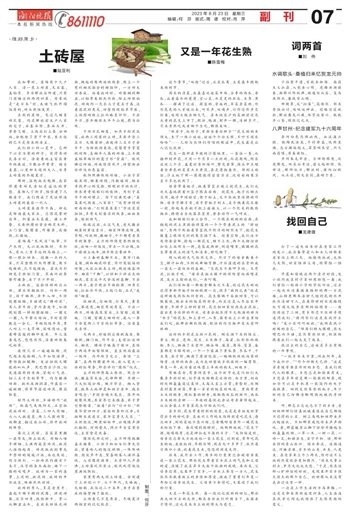■陆亚利
我知事时,屋场有十几户人家。清一色土砖屋,无石基,盖稻草。多为解放后所建,只有门前塘边的两间旧屋,老辈说是“走日本”时,未被飞机炸塌仅存的,砖头剥蚀发黑。
去别的屋场,见过几幢青砖瓦屋,均是解放前大户人家的宅子,石基石阶,条石天井,重脊飞檐。土改后打土豪、分田地,分配给了贫下中农,里头住的已不是原来的房主。
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种下以穷为荣的种子,觉得青砖瓦房古旧,涂染着地主富农奢华的痕迹,不敢公开赞赏。暗自羡慕,心里却又趋同大人,安享土砖屋的冬暖夏凉。
那时,温饱尚且勉强,农家修建青砖瓦房似是遥远的梦想。屋场人丁渐多,陆续建了几栋房子,我们便成了见证修造土砖屋的最后一代人。
土砖屋虽造价不高,却也是缔造最大家业,总得花费好些年,积蓄谷米菜蔬,请工开餐。又要积攒些资金购买木料,立门窗,架檩梁,作椽条,设楼枕,扎楼板。
屋场属“见风消”地带,不产木材,无以就地取材。买杉木,需从三里多远的马路上,一根一根扛回来。拮据一点的人家,只买整根杉木作檩梁,架不起楼枕,扎不起楼板。甚或买杉树尾子拼制门窗,买南竹剖条替作椽条,省下不少开销。
立秋后,选黏性好的边山田,灌水犁翻耙烂。闷水一两日,排干晒熟,牵牛入田,不停绕圈踩踏,乡语谓之“蹧砖泥”。男人牵牛绹,拿竹条赶牛,如持规划圆一样转圈踩踏。一圈又一圈,人牛晕头转向,不时需得歇息一会儿。牛绹绕结牛角,男人叼上一支旱烟,深吸慢吐,望着蜂窝般的脚印发呆。牛儿荡着尾巴,悠悠然然,沿着田埂卷吃枯草。
连续几日一遍遍踩踏,泥巴越来越黏稠,人牛如陷沼泽,费劲拔扯腿脚,发出扭脱火罐般的叭叭声。泥巴隐去沙性,似发透揉熟的老面,冒起小气泡。切三五寸长稻草节,均匀撒满田面。挑水泼洒润湿,作最后一遍踩踏,将草节揉进砖泥,强筋防裂。
制作土砖坯,乡语称作“放砖”。秋高气爽艳阳天,正宜挑泥放砖时。清晨,三四人荷锄,七八人挑箢箕,两三人提砖架、端脚盆,翻过后山岭,排开放砖的阵势。
每次上泥前,在箢箕里撒一层草灰,防止粘泥。荷锄人唾手挥锄,上满两箢箕砖泥,挑泥人挂钩起肩。砖泥挑放到事先平整好的缓坡沙地,由远及近,均匀排列。一担砖泥约摸百十来斤,压弯的杂木扁担,洒下一路的吱嘎声。放砖为一家的喜事,上泥的、挑泥的、放砖的开怀说笑,场面热热闹闹。
放砖的男人,多是老里手。盘起不稀不稠的泥团,摔进砖架,压实四角,扶框擀平。掌心从脚盆沾水,左右来回抹光砖面,拽起砖架两端的绳套,摁上一个有利砌泥黏合的拇指印,一方砖大功告成。接着放砖时,砖架搁到脚盆,以稻草卷刷洗内框,防止砖框粘泥。砖块约一尺长七寸宽五寸高,泛着湿泥的亮光,四壁隐现稻草节痕,上端因砖框上拉而略呈凹形。不出半日,整齐铺排大半个山坡,蔚为壮观。
千砖万瓦砌屋,如燕子衔泥筑窝,放两三间屋的土砖,多要辛苦三五日。天缘若好,满坡砖三五日才会半干。为防秋雨袭扰,需留有手掌宽的间隙,垒砌半人高的砖墙,上头披盖稻草编织的篦子形“管扇”。秋风拂过砖墙,砖块慢慢风干,砖壁淅出些许浅白色盐霜。
秋阳照拂垛垛砖墙,小孩子穿梭其间,贴着砖缝,闪躲嬉闹,相互寻找开心的笑脸。刚刚识字的伙计,传承哥哥姐姐们的伎俩,用钉子在半干的砖壁上,写下经典咒语:“某某某吃狗屎,八百筒!”还有泄愤的时尚标语:“打倒某某某!”字迹歪歪扭扭,多有叉划磨消的线条,斑斑杂杂,铭刻稚气。
秋收过后,云淡气爽,老天腾出砌屋的黄道吉日。砌匠师傅进场,戴草帽,叼纸烟,操砌刀,个个都有老里手的架势。主刀的师傅焚香燃烛化纸,放响一封炮仗,宰杀一只公鸡,合十请动土地爷,拱手默念鲁班爷。
小工备好基脚片石,架牢门板支架,调和砌泥砂浆。用竹篾铰接的砖架,从后山挑来土砖,码放墙基内外。砌匠“下脚”,以拌和少许石灰的砌泥,浆实筑平尺余深的基脚。不出一两日,房子现出平面轮廓。四角定桩,拉扯水平线,立起门框,正式“走砖”砌屋。
抹砌泥,勾砌缝,打角尺,量靠尺,赛进度,砌匠有说有笑。不出一两日,砖墙高及窗台,立窗框,设架板。门楣、窗楣上砌砖时,嵌入一条寸余宽两三寸长的红布条,渲染喜庆吉祥。
又两日,砖墙到达楼枕高度。架楼枕,搁门板,作平台,支撑扯送砖头、砌泥。横垛子略高于檐口,直垛子两端开始留梯级,直至顶端最后一块砖。内外垛子完工,脊顶“上梁”,在两侧檩梁外端,嵌入宽大一些的红布条,即告举行“圆垛”仪式。
主刀的师傅高立脊顶,默念口诀,撒盐茶米谷,礼神辟邪。手持一只大红冠公鸡, 嫩刀宰杀,抛入堂屋,敬奉土地神灵和祖宗老爷。拖长音唱念:“手提金鸡头尾长,张开双翅像凤凰;东家养它来报喜,弟子拿它祭栋梁。”接着“出灯”讨口彩:“新屋华堂四四方,梁柱桁条积沉香;日招财来夜进宝,荣华富贵久久长。”点燃炮仗,噼里啪啦中,公鸡随声挣扎翻跳。时间愈久,预示平安富贵长远,主家愈是欢喜。
圆垛礼毕之时,主刀师傅抛撒喜庆糖果。小孩子和妇女们争先恐后,冒着呛人的炮仗硝烟,一阵阵哄抢。炮仗声平息,贺喜的客人满怀喜悦,入座圆垛酒席。禾堂坪人声鼎沸,土砖屋屹然耸立,秋风吹得炮仗屑满地飘红。
家里有两大间土砖屋,分别建于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无楼板,无粉刷。我住过二十来年,亲手在靠床的墙壁糊了报纸。
土砖屋已不复存在,冬暖夏凉两相宜的记忆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