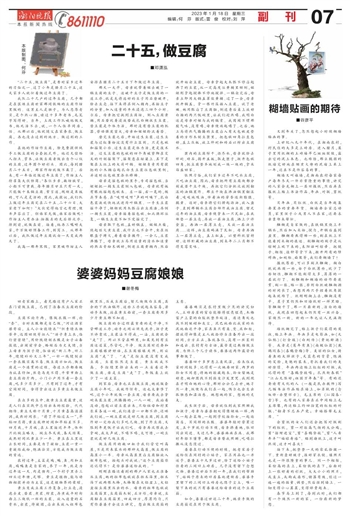■邓潇泓
“二十五,做豆腐”,是昔时家乡过年的习俗之一。过了小年是腊月二十五,这天家乡人就忙着做过年豆腐了。
我队二十几户的过年豆腐,几乎都是在匡姓豆腐世家那间低矮的豆腐作坊里做的。这男主人是独子,为人忠厚老实,是个热心肠,读过十多年老书,毛笔字写得好。当年,土改工作队喊他做文书,他死活不去,说,一个人住单间房,怕。从那以后,他就随父在家务农、做豆腐,再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做过别的工作。
在他的作坊作豆腐,除免费提供纯手工做豆腐的全套把式外,他还无偿给人指点、掌本,让做豆腐者做出自个心仪的豆腐,过年图个好彩头。因此,每到腊月二十五日,那家作坊就做不赢了。后来,有一年临近做过年豆腐了,作坊主人特召集大伙协商:“各位乡亲,敝坊狭窄,小船不可重载。每年腊月廿五只有一天,只能做十来锅豆腐。常言道,规矩是呆板的,可人是灵活的。因此,我提议,我们队上做过年豆腐定在二十五、二十六日。大家意下如何?”大伙觉得他言之有理,便齐声答应了。但谁家先做,谁家后做呢?作坊主人有办法:按报名的先后排次序,排到前,就做在前。接着,他再三嘱咐大家,千万做好预备工作,别窝工。从那年以后,我队做过年豆腐就由一天变成两天了。
我高一那年寒假,家里被作坊主人安排在腊月二十五日下午做过年豆腐。
那天一大早,母亲就带着姐去破了一锅豆腐的豆子。这破干豆子是做豆腐的一道工序,就是先将选好的豆子用石磨破开,除去豆壳。接下来将其倒入桶内,再按豆子的分量,加入适量的井水浸泡三四个小时。尔后,母亲把它挑到豆腐坊,倒入豆腐黄桶,用石磨就着浸液磨成乳白糊状生豆浆。磨豆浆是个体力活,那时没有磨豆浆的机器,劳动强度蛮大,母亲和姐姐轮流着磨。
磨完豆浆之后,开始过生豆浆。过生豆浆与过红薯粉淀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包袱和摇架小些。过生豆浆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过生豆浆的包袱的四个角被紧绑在交叉的竹制摇架下,摇架悬在坊梁上。其下是架在土灶上的大荷叶锅。姐姐负责用有提把的小木桶舀起乳白生豆浆往包袱里倒,并适时往包袱里添水释稀。
母亲是摇包袱的里手,专司摇包袱。当姐姐把一桶生豆浆倒入包袱,母亲就有板有眼地摇起包袱来。左一摇,右一晃的,极具节奏感。在“吱呀吱呀”声的叫唤下,乳白色浆液欢快地流进荷叶锅里。一手生豆浆摇干净了,姐姐就用木瓢舀出豆腐渣,再倒一桶生豆浆,母亲接着摇包袱。如此循环往复,一锅生豆浆不知不觉摇完了。
母亲取下包袱,盖好锅盖。姐姐点柴,烧起旺火煮豆浆。我什么也不会干,坐在灶眼盘子烤火,看着母亲操作。一会儿,豆浆沸腾了,母亲就立马用适量的清水和适量的熟石膏粉末调好,倒进豆腐黄桶内。然后就开始汆豆浆,母亲拿起大木瓢不停舀起沸了的豆浆,从一定高度往黄桶里倾倒,姐姐则拿起搅捧不停地搅拌。一锅汆完后,母亲立即用大锅盖罩住黄桶。过了一会,母亲掀开锅盖,拿一根竹筷插入豆浆,试了老嫩。她用瓢舀了豆腐脑,倒进身后桌上放好白糖的两只饭碗里,让我们趁热喝。我明白这是母亲对姐与我的犒赏。我因闻不惯那股气味,没有喝,母亲便端起喝了。之后,她立马将热气腾腾的豆浆舀入有大包袱皮垫着的方形木制豆匣里,把包袱四角拉直包好,盖上压板,放上秤砣和砖石以榨出豆腐水。
匣内的豆腐榨干、沥尽水,母亲就除去秤砣、砖石,揭开盖板,取走匣子,掀开包袱四角,把豆腐整齐地划成一块一块的,拿米筛盛回家。
依照习俗,我们家乡过年不吃水豆腐,只吃油豆腐。因此,母亲把所有豆腐块都分割成若干豆干块,再把它们分批次放到翻滚的油锅里炸。那豆干块在沸油锅里翻滚着,吱吱地吸油,伴着油的芳香逐渐膨胀、脆黄。这时,母亲将它们捞起沥油,放入盘子。直到那锅水豆腐全部炸成油豆腐。留足过年的油豆腐,母亲便拿来一只瓦缸,在底部垫一层豆壳,再放一层油豆腐,洒上少许食盐,再洒一层薄豆壳,又放一层油豆腐......这样,油豆腐码满了瓦缸。母亲再洒上一层薄豆壳,盖上缸盖,以塑料纸密封好。这样贮藏的油豆腐,到来年二三月都不得变霉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