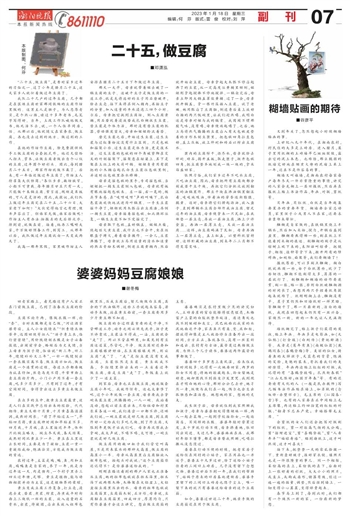■谢冬梅
回老家路上,看见路边有户人家正在门前做豆腐,已到了准备压豆腐的阶段。
豆腐不论斤两,像做衣服一样,论“套”。古时衣服都是自己做,“河边酒家堪寄宿,主人小女能缝衣”“织素缝衣独苦辛,远因回使寄征人”“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用针线缝制衣服是女子必备技能,出阁前学会,婚嫁后为丈夫缝,当上母亲为孩子缝,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针一线缝制出一套衣服实属不易。做豆腐亦如此。做豆腐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每道工序都要极为认真仔细,丝毫马虎不得。平常市面上卖豆腐论斤两,小门小户用不着一套豆腐,吃多少买多少。只有到了过年,才有空闲时间,舍得拿出这么多黄豆来做豆腐。
在众多的豆中,数黄豆豆浆最重,这是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代代相传。黄豆又称十月黄,十月黄喜高温湿润,成熟时间长。“莳了早稻过五一”,早稻四月莳,黄豆栽种时间和早稻差不多。四月栽,十月收,在土里接近半年,体积只比豌豆略大。豌豆冬天栽,春天结果,成熟时间比黄豆少一半。黄豆在土里这么长时间,主要是为了凝粉,豆浆一重一重凝结成粉,饱满壮实,方能成为做豆腐的首选。
农村过年,主菜是鸡、鸭、鱼、肉和豆腐,鸡鸭鱼是自家的,养了一年,就是为过年这一天。肉是猪肉,一个村子里杀三四头过年猪,足够。黄豆是植物,能与动物相提并论为主菜,这是植物界的荣耀。
黄豆变成豆腐工序复杂,打豆壳,浸泡去皮、磨浆、煮浆、榨浆,再煮成平时街面上三块钱一杯的豆浆,放入适量的石膏水,汆浆,待凝固,舀出来放入粗布包袱里压,压成豆腐后,留几块做白豆腐,其余的下热油锅炸。这些工序说起来容易,若动手来做,站在黄豆面前,一套豆腐要用多少斤黄豆都不知道。
做豆腐的全过程最重要的是干净,不管哪道工序,动手之间必须先洗手,孩子更不许靠近,豆浆沾不得咸,一沾,豆腐就会“走”了。所以不管在哪里,如果见到有豆腐这道菜,尽管吃,干净。做豆腐时还要和豆腐娘娘讲好话,求豆腐娘娘关照,别让豆腐“走”了。“走”是指豆浆没有变成豆腐,豆浆依然是豆浆。黄豆收成不高,手指缝里挤出来的一点省着过年做豆腐,若是豆腐“走”了,年饭桌上就少了一道主菜。
到家后,母亲也正在做豆腐,她说做套豆腐小年吃。我故作惊奇,这也太奢侈了吧,过个小年就做一套豆腐。母亲要我去拿碗来装豆浆,热腾腾的,一人一碗。我站着没动,想起以前豆浆出来,只给祖母和村里长辈各送一碗,我们连尝一口都不许,还哄我们说,一碗豆浆就是好几块豆腐,到豆腐炸好一定给我们多吃几块,到了炸豆腐,又限到年更饭才让我们吃。母亲再次催我去拿碗,我大声说,不喝不喝,太可惜,一碗豆浆就是好几块豆腐。
做豆腐用的敞口缸子我们管它叫高屋,不是用来装水的那种大高屋,做豆腐的高屋小一半。母亲从高屋里舀豆腐脑放入粗布包袱,抬起头对我说:“这个豆腐箱你还记得不?是你婆婆送给我的。”
刚刚在路边看到的那户人家也正准备压豆腐,她的粗布包袱放在粗禾筛里,粗禾筛下放两根木棒,木棒架在大铝盆上,大铝盆接豆腐里压出的水。母亲的粗布包袱放豆腐箱里,豆腐箱木制,正方形。母亲说,豆腐脑在豆腐箱里,四成四方,厚薄均匀,只有你婆婆才会这么讲究,想出做豆腐箱的主意。
婆婆确实是农村里极少见的讲究妇人,土砖房屋的窗台能擦得锃亮锃亮,木格窗户上蒙的白胶纸整齐皎洁,连边角处也找不到皱褶和灰尘,泥巴地面比我家的水泥地面还干净,家具虽只有桌、凳、床和柜,摆放得却像是主人收拾停当准备外出一段时间,方方正正,各就各位,没有一丝歪斜和逸出。农村有句古话,最苦莫过熬糖做豆腐。为供三个儿子读书,婆婆这两件最苦的事都做了。
婆婆四十多岁患上类风湿,后来住我家时间较多。记得有一次她要回家,两岁的孙女不同意,将她的鞋藏起来。孙女留她是好意,她却因找不到鞋坐沙发里哭。我到现在才明白她的心情,那时公公已去世,她孑然一身,纵便与我们在一起,偶尔也会生出孤独感和漂泊感。她想她的家,想她的丈夫。
我生孩子后,母亲就住到我家照顾我和孩子。母亲与婆婆相处得像姐妹一样,两人一起去菜场,一起到学校接孙女,一起逛商店,买同样的衣服。婆婆年轻时劳累过度,五十岁就行动不便,母亲搀着她,依旧同出同进。又过几年,婆婆瘫痪在床。我那时年轻不懂事,都是母亲替我照顾,吃喝拉撒从没怠慢过。
婆婆在行动不便的时候,把老家房子送给住在同村的小姑子,家具用品也一并送予。婆婆五十九岁过世,除了送给小姑子住着的三间旧土砖房,几乎没有留下念想之物。婆婆过世后不到一年,在我们的帮助下,姑妈于原来的旧房基地建新房。婆婆手里留下的三间旧土砖房也隐于尘土,唯一留下来的就只有婆婆送给母亲的这个豆腐箱。
如今,婆婆过世近二十年,她亲手做的豆腐箱还在用于做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