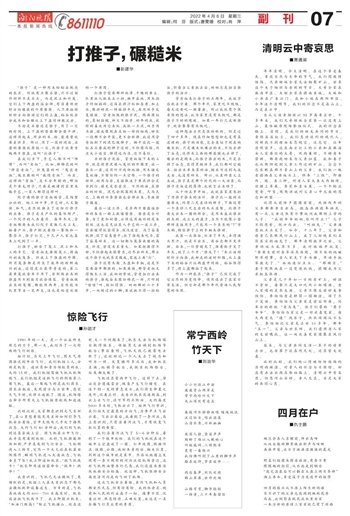■彭建华
“推子”是一种用来给稻谷脱壳的农具。形状有点像石磨,只不过制作材料不是石头,而是泥土和竹篾。它们上下两盘的接合部,有沿着顺时针方向镶嵌的竹质磨齿。人只要按顺时针方向推动它们的上盘,稻谷就会分成米和谷糠从上下盘间四散流出。
不论是石磨还是推子,用了一定的时间,上下盘的磨齿都会磨平掉,这样用起来,所出的米、粉、浆质量就要差许多。所以,用了一段时间后,石磨的磨齿就要铣一次,而推子就要重做两片磨盘,这叫“打推子”。
在我们乡下,手艺人都不叫“师傅” ,而叫“老叔”。比如,弹棉花的叫“弹匠老叔”,织篾器的叫“篾匠老叔”,做衣服的叫“裁缝老叔”。而且,这样的“老叔”,是不分年龄的,哪怕是个黄毛伢子,只要是被请到家里来做手艺,一家人都得这样叫。
院子请的推子老叔姓管,是隔壁公社的。他三四十岁,手艺好,人又勤快、和气,自然就独占了这份打推子的业务。推子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一个院子的人共着用。每年冬天,管老叔都要来我们院子里做几天工夫。按着户头,每户轮流着陪一餐饭和一餐茶点,推子打完,十几户人家也基本上吃到了一半。
打推子,融合了篾工、泥工和木工的手艺。管老叔先要做篾工,将南竹剖成篾条,织成上下推盘的外围。所用篾条都是用长了数年的新鲜南竹剖成,还得是头层带青皮的,第二层黄篾就舍弃不用了,否则做出来的推盘用不到数月就会爆裂。管老叔做出来的篾围,都能用两年,自然能为队里节省一笔开支,这也是他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打推子需要那种纯净、干燥的黄土。队里派人挑来五六担,摊开在地,用木拍子仔细拍碎,过筛去掉沙粒和杂质,加上水,像拌砖泥一样踩拌半天,再用双手反复揉搓。管老叔做的推子泥,跟面团似的,柔韧黏糯,却又不粘手。幼年的我,就特别喜欢用它来玩。我抓一点泥,双手用力搓,搓成像现在米粉一样的细线,好长一段都不会开裂,更不会断掉。我还用管老叔剩下的泥巴做弹子,晒干后比一般红石头磨成的弹子还好,不但圆而轻,而且大小适宜,弹得远而准,还不易烂。
弄好推子泥后,管老叔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黄泥填入篾织的外围里。放一层压一层,还用竹刀使劲地插,用木锤反复地锤,不留任何一点空隙。一个推子的好坏、耐用与否,直接取决于黄泥拌合是否到位、填充是否密实。不然的话,在推谷的时候,泥巴会脱落到米里,久而久之,上面的竹条磨齿也会掉出来,导致推子报废。
最后一道工序,是在两片磨盘接合部的各自一面上嵌镶磨齿。磨齿是全竹条,为了更加耐磨,必须选用南竹的蔸来削制。这也是见证匠人手艺的一道工序,需嵌镶得疏密得当、深浅适宜。浅了容易脱掉,深了容易磨平;疏了推起来吃力,密了容易碎米。这一切都与篾条嵌镶的高度、斜度、密度关系重大。如果把握得不好,不但推起来很费力,还尽出碎米,那么这个推子也就算是报废,需返工再“打”。
推子还有木架、木盘和手柄,这是不需要每年都换的。如果要换,那管老叔又得做木工活。我奶奶常说,管老叔打出来的推子,推起谷来跟纺棉花一样,只听到“嗡嗡”叫,轻松得很。奶奶那时六十多岁,一双缠过的小脚,虽说挑不得一担稻谷,但每当父亲挑去后,奶奶总是担当推推子的活计。
管老叔来打推子的头两年,我放学后就去守着。那个年代,家里吃不饱饭,每天还要吃一顿薯渣,所以我就有个很奇怪的想法,认为家里没有米饭吃,都是推子不好的缘故。如果一年打几次新推子,就会餐餐有米饭吃。
这种想法当然是很幼稚的,但是过了四十多年,现在仔细想想却也是有其道理的。推子的功能,完全类似于现在的碾米机。只是碾米机碾出的米,不仅去掉了谷壳,还将米上面的那层膜也去掉了,碾出的是精米;而推子推出的米,只是去掉了谷壳,显得黑糙许多,我们都叫它糙米。按出米率来算的话,糙米可达到九成左右,也没有碎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推子真是那个时代的一大功臣,而推子老叔受到厚待,也就言正名顺了。
从十四五岁开始,我就在家里承担了用推子推米的活计。推子比一般的石磨要大,约有二尺直径的样子,下面还有一个直径三尺左右的木头座架,比推子要大出来一圈的部分,是用来盛放推出的米的。这么大的盘子,当然不能像小磨那样直接用手,只能用一个长长的“7”字木钩,钩住推子上的手柄来推动。
我第一次推谷,忙活了半天,弄得满头黑汗,就是不出米,连谷壳都不见半瓣。后来,一位堂嫂见了,捂着肚子笑了半天,说了三个字:“推反了!”本应该顺时针方向推,我却走的逆时针路,从上盘下来的稻谷只往两盘中间转,稻谷堆得多了,将上盘都抬了起来。
作为一种农具,“推子”已经完成了它应尽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了农家日常生活,但它却是那个年代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