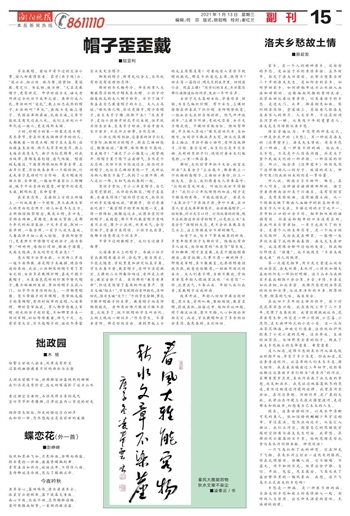■陆亚利
穿衣戴帽,看似平常不过的生活小事,国人却看得很重。蒙学《弟子规》云:“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尤其是戴帽子,更有讲究。中学时读古文,语文老师讲过古时孩子成年之前,要举行成人礼,男孩的叫“冠礼”,戴上标志成熟的帽子,女孩的叫“笄礼”,盘起头发插上簪子。民国后革新鼎故,礼数日减,父辈可能就没有见过成人礼,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拨人,更是闻所未闻。
少时,对帽子的第一印象是虎头帽。寒冬季节,背在怀里或蹒跚学步的幼儿,大都戴着一顶虎头帽。帽子呈头盔形,后向披盖至后颈。两只毛茸茸的虎耳,朝上支棱出虎虎生气。面子为红花棉布,衬底为绒布,薄棉夹层绗缝,透气保暖。帽檐绒毛镶边,下檐有两根细红布条系带。左右耳位置,用红线各垂吊一只银铃铛,行走或身子晃动时叮当作响。虎头帽连同猫头鞋、长命锁,一般由外婆家打三朝赠送,赋予平安吉祥的寓意,祈望外孙虎虎生威、聪明机灵、长命富贵。
农家虽清寒,五屉柜上方的土砖墙上,一列地挂着一个镜框,里头嵌满全家人的黑白纪念照片。幼儿如是冬天生日,去照相馆摄影留念,戴虎头帽,系口夹,穿棉衣棉裤,罩围兜,着猫头絮鞋,是那个年代的标准装扮。十天半月后,取回一张单照、一张合照,一家子人欢天喜地,几番品评才细心嵌入镜框。亲朋邻舍登门,见着照片中懵懂可爱的孩子,竭力夸赞:“哟哟哟,咯相打得好,眼珠子溜圆,天庭又饱满,长大哒肯定有出息!”
虎头帽不分男女款,小孩两三岁后一般不再饰戴。若是帽子未破损,便会传递给弟妹。此后,小孩御寒的帽子有了男女之别。女孩多是戴棉纱帽,甚或干脆不戴帽子,头裹各色花样的纱围巾替代帽子,展示稚嫩的美丽。男孩的帽子五花八门,似乎作为男性的标志,一律都有帽檐。有不带褡子的单棉帽,有带绒毛褡子的薄棉帽,有内衬绒布的皮帽、人造革帽。那时崇军尚武,男人都梦想戴上军帽。稍大的孩子赶时髦,不知哪里弄来一顶旧军帽,松松垮垮戴着,神气十足。也有家里太穷,买不起帽子的,临近冬季蓄长头发充当帽子。
御寒的帽子,附有礼仪含义,自然就有些没有道理的忌讳。
那时的冬天格外冷,年长的男人大都戴厚实的呢子帽或东北帽。小孩子对翻卷绒毛的大人帽子好奇,冷不丁摘下沓盖在自己戴着帽子的头上。大人立马说:“咯死徕几呃,你还冇换牙,帽子沓帽子,会生夹牙子嘞,快取下来!”生夹牙子,是指小孩换牙时乳牙还未脱,恒牙就并排长出来。生夹牙子好痛,日后牙齿又长不整齐,不是什么好事,当然忌讳。
小孩之间闹别扭,受委屈的孩子们无可奈何,抓取对方的帽子,朝自己裤裆绕过,狠狠地说:“看啰,咯你都长不高哒,变成矮子!”满足了小小报复心,赶紧跑开。将帽子置于胯下沾染秽气,当然是个大忌讳。伙伴不依不饶追过去,抓住对方的帽子,也往自己裤裆里绕一下。或许认为俩人都长不高了,找到了心理平衡。两人追打一阵,又和气地玩耍到一起。
男孩子贪玩,不小心弄歪帽子,自己没有觉察到,伙伴趁机取笑:“帽子歪歪戴,老婆来得快!”继而得寸进尺,抓住伙计的手笑嘻嘻地说:“握握手,你讨老婆我吃酒!”戴歪帽子的男孩尴尬一笑,羞得一脸绯红,拔腿追过去,试图弄歪同伴的帽子。我猜想,那个年代戴歪帽子意味着不正经,像个小流氓,水里水气,会勾引妹子,老婆才来得快。小孩子也自尊,谁都不情愿有这个坏名声。
平常不过的戴帽子,也衍生过诸多趣事。
父母看重头上的帽子,告诫小孩子穿衣戴帽要遵古训、合礼节,整洁周正,不能太随意。学校里更加讲究仪表穿着,学生衣着不整,戴歪帽子,老师不准进教室。上课的二次预备铃响过,老师走上讲台,教室安静下来。虽然那时“教育要革命”,但还是保留了基本的师道尊严。值日生喊“起立!”,学生脱帽向老师敬礼,老师回礼,值日生喊“坐下!”个别学生偷懒,事先不解开帽褡子的系带,戴着帽子向老师鞠躬敬礼。老师有时睁只眼闭只眼不在意,次数多了,把不脱帽的学生叫出列,上纲上线地一顿训斥:“作为学生,不尊重老师,那是你的自由。看到黑板上头的毛主席像没有?对着他老人家你不脱帽就敬礼,那是不热爱毛主席,晓得不?回去写一篇检讨,明天交到我手里。回到座位去。现在上课!”同学们的目光,齐齐聚焦那位满脸通红的同学,发出一片咋舌声。
女孩子天生喜好女红,学着母亲、姐姐,为自己编织纱帽。有个女生,上课时偷偷在讲桌底下织纱帽。老师明察秋毫,一把扯出毛衣针当场折断,怒气冲冲地训斥:“上课不听讲,考试吃零蛋。女子无才便是德,干脆回家做女红,绣双贺郎鞋,早点嫁人算哒!”眼见前功尽弃,自知理亏,女同学不敢放声大哭,埋头伏在课桌上抽泣。男孩子搞小动作,老师没收弹弓、洋枪、蚕宝宝时,女生们总是幸灾乐祸。此时的男孩子们,悄悄对着女生们做鬼脸,心里一阵窃喜。
那时,大队经常开批斗大会,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上台挨斗,都要戴上一个纸糊的高帽子,上面标示身份,打上一把大叉。会上,我们跟着大人举拳高呼:“打倒地富反坏右,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小小年纪便隐约知道,帽子是个敏感的东西,不能乱摘乱扩。若是与“五类分子”子弟闹矛盾,争吵不赢,出口骂人家是反革命狗崽子,永世戴高帽子,一招制胜,对方无言以对。打闹玩耍的时候,绝不去抓抢这些同学的帽子,以免犯上为“五类分子”摘帽的大忌,更不会抓来戴在自己头上,沾上阶级成分不好的晦气。
知青下放,给乡下带来城里的时尚。乡里年轻男孩子大都朴实,偏偏也有许多人逆反,效仿城里的“水老倌”留长发,穿杆脚裤。帽子歪歪戴,或是干脆把帽檐朝后,昂首挺胸,凡事不屑一顾的样子。即便是军帽,虽不敢戴歪,也要将帽檐捏拢压低,故意遮住眼眉,一副故作深沉的派头。大人们看不惯,当面不敢说,背地里责骂年轻人跟城里流氓“水老倌”一样,流里流气,不务正业。年轻人我行我素,歪戴帽子遂成时尚。
改革开放,年轻人纷纷学港台赶时髦,烫头发,穿喇叭裤,架蛤蟆镜,戴歪歪帽,提收录机,招摇过市。起初非议四起,碍于潮流汹涌,势不可挡,人心和舆论渐渐淡定。此后,穿衣戴帽卸去了多余的社会负荷,各色各样,五彩缤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