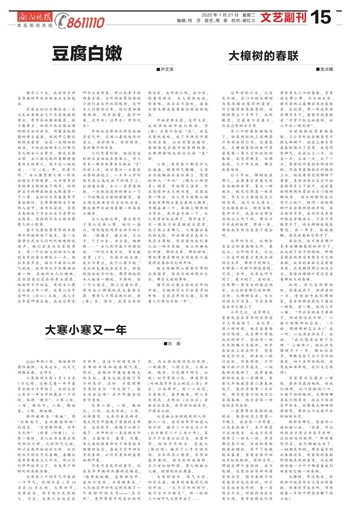腊月二十五,我的家乡许家吊楼的年味渐渐由淡变浓起来。
家庭主妇们大都在这一天从瓦缸里取出几个月前收藏的黄豆,有节奏地颤动簸箕,把干瘪黄豆、细泥沙与滚圆滚圆的肥豆分列出来,用撮箕把肥圆的黄豆盛着,端到早已擦洗好的石磨旁。这是一道精细的粗活,不知底细的男人们唯恐自己的女人太费力,抢先去推石磨。女人微笑地斜着眼睛看着自己的男人,漫不经心地说道:“行(走)开,你奈不何。”女人像掌握火候一样地控制豆子的数量,从石磨里出来的黄豆刚好成了两半,而保护豆子的那层细皮也脱落得一干二净。主妇们又用簸箕有节奏地颤抖,光滑黄嫩的豆子被倒入盆中,再用水浸泡,清亮清亮的地下井水让豆子身骨松泛起来,浸润的半边豆瓣活像婴儿的小脸蛋。
整个大屋数量有限的石磨都不停地转动了起来,每一石磨旁边是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她们在互比自家的黄豆。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看到自家的黄豆颗粒小一点,她拉长着声音,抬头不看别人娇气说道:我家的豆子就像满姑娘一样。其他的女人打趣她,是你漂亮还是你的黄豆漂亮,她始终不作回答。有的女人像是汇报工作一样,我男人过年爱呷订(实心)豆腐, 我儿子过年爱呷油豆腐,我女过年爱呷水豆腐煮鱼,所以我要多做两套豆腐。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小孩们在禾坪玩得起劲,突听大人们提到过年,他们更加蹦蹦跳跳,双手拍着,高声叫着,过年乐!过年乐!有肉吃乐!
年味就这样由淡渐浓地融在空气中,它满心喜悦地告诉青山,告诉绿水,告诉树林,告诉留守的百鸟。
人们凭着经验,把浸泡适时的豆盆端放在磨架上,男人拿来一根长长薄动木做成“T”形的工具,把它圆口一头套在石磨的拐把上,一头半工字形固定在从高处放下的绳子上,拉动着石磨。女人一手掌着拐把,一边把浸泡好的黄豆一勺一勺地喂进石磨的磨眼里,磨石周边挂满雪白雪白的白浆,像池塘中水旋涡叠圈一样落进王桶里。
大人也盼过年,磨豆腐对于男人是养心事,他们一高兴,便唱起民间草台班子的小调:“张懂古,磨豆腐,王豆子,丁丁口当 ,水豆腐,嫩秧秧……”女人则徉装不耐烦地说:“叫化子发穷欢,冒米敲筒贯(子),你推你的豆腐,发欢不费力,我个人推不起。”真正的夫妻组合没关系,拼装的组合就不行啦,那掌拐把的女人把活一搁说,不推啦,你一个人磨去,脸上泛着红晕,因为这小调唱的是夫妻磨豆腐。那男人只得求她们说,推(磨)乐,推乐,我冒占你的便宜乐,我听别人唱,我口痒,跟着唱两句。女人嗔怪地说,你再唱,我当真不推啦,接着石磨又像发春雷般似的滚动起来。
开始煮沸豆浆,没开火前,我母亲就招呼我们姐弟,作(做)豆腐不准说“走”,说走豆腐就走啦,成了半液态半固体的豆腐。往灶堂里添柴时,要剔除夹在柴中的香樟树柴,大概樟脑味也会让豆腐“走”掉。
入夜,各家各户都是炉火红通通,锅里热气腾腾,父母合力把桶抬放在灶面上,慢慢地倒入“牛四”(锅大小的型号)锅里。开始慢火温煮,然后慢慢加大火的力度,豆浆滚沸一阵后,大人用大的瓢从锅里把煮沸的豆浆舀着倒入桶里,用锅盖捂一下,再洒上煨熟的石膏水,再用盖子捂一下。大人觉得时机成熟了,揭开盖子,用一根筷子垂直插进豆浆里,筷子挺立在那儿。父母露出喜悦的笑脸,诉说请逝去先辈人来尝豆腐脑,然后再给我们每人舀一碗豆腐脑。放上白糖或红砂糖,那份豆香,那份甜味,那份滑溜是那时乡村农家人最值得欢喜和记忆的年味。
把豆腐脑倒入垫着纱布的豆腐箱里,再用石块砖稳压扎实,那是父母的事啦。
腊月的石磨豆腐就是年的开始,它抛砖引玉引出更多的年味。它就是年的大旗,引领着人们奔向目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