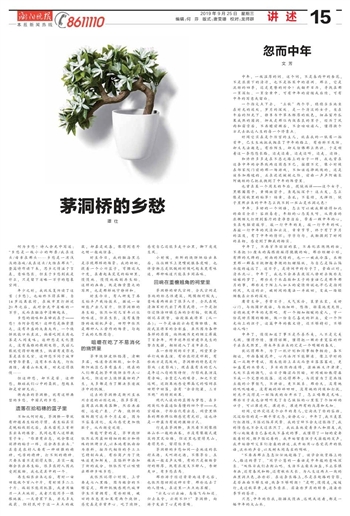何为乡愁?诗人余光中写道:“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整篇诗作读下来,思乡之情溢于言表,意味悠长。但至于乡愁到底是什么,只是留下省略一万字的想象空间。
年少之时,我就反复拜读了这首《乡愁》,也始终不得其解。自14岁远离农村,在城市里打拼近20年之后,我对余光中省略的一万字,反而在脑海中清晰起来。
乡愁的韵味和真谛就在于——愁!为何会愁呢?这种愁是物资匮乏,没有丰盛的大鱼大肉,一个烧饼就能口水直流,倘若吃到豆腐也算是人间美味;这种愁是文化匮乏,没有高雅的歌剧电影,民谣儿歌就觉得妙趣横生,倘若有皮影也算是其乐无穷。这种愁不同于城市的繁华景象,没有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看着山水发呆,时光过得很慢……
但这种愁,却不是苦。这种愁,触碰我们心中的柔软,想起来却是甘甜无比。
衡南县的茅洞桥,就有这样典型的乡愁,中国式的乡愁。
遗落在拾稻穗的篮子里
不知从何时起,茅洞桥一带就有种植再生稻的习惯。再生稻其实是晚稻收割之后,在禾苗蔸上重新长出来的粮食。民间也有人这样教育子女:“你若有出息,就会像这割掉的稻子一样,还会再长出来。”其意是农村人要有一种顽强的精神,吃苦的精神,打不倒的精神。只要禾苗不是割得太狠,其实一般都会长出再生稻,很多农村人因此受到鼓励,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再生稻长出来之后,有时一亩田能收个百八十斤,有时顶多二三十斤。收割不能用机器,或者用镰刀一点点地割,或者只能用手一根根地拔。一天劳累下来,并无多大收获。但村民对于这一点点的收获,却甚是欢喜,像得到意外之财一般地惊喜。
时至今日,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那样的场景:我的奶奶,提着一个小竹篮子,弯腰近九十度,在看起来荒芜的稻田里,慢慢地、慢慢地收割再生稻。这样的画面,既是物资匮乏的写照,也是那样地宁静祥和。
时至今日,有人研发了再生稻丰产栽培技术,据说一亩田能产出几百斤。但茅洞桥的再生稻,依然如同几百年以往的味道,任其生长,没有轰隆隆的收割机声音。田野中依然是那种人工劳作的场景,勾起了我的无限思念。
咀嚼在吃了不易消化的烧饼里
茅市烧饼皮酥馅薄,清晰多层,味道香浓酥软,如今在衡阳地区已享有盛名。现在的人们都是把茅市烧饼当作点心来吃,但这世上烧饼最初的产生,大多都是为了解决长途跋涉中的饥饿。
过去的茅洞桥是衡州至永州古道的必经之地,很多茶商、盐商在此歇肩落脚,然后再启程,远赴广东、广西。烧饼的保鲜期可达半个月左右,因为不容易消化,反而感觉更加饱肚子,从而颇受欢迎。
难能可贵的是,茅市烧饼依然采用最初精细的配方和特殊的烘烤方式,以本地有机面粉为原料,按历代相传的手工工艺精制而成。有些商户为了使味道更加鲜美,在馅料中添加了新的成分,但依然可以咀嚼出那种乡味乡愁。
我依然记得小时候,上学要走七八里路。因为粮食的不够富足,那种饥饿感现代城市学生不曾拥有。有些时候,破旧的书包里如果有两个烧饼,感觉真是非常开心。吃了烧饼,感觉自己还能多走十公里,脚下虎虎生风。
小时候,新鲜的烧饼烘焙出来后,往往顾不上烫嘴就狼吞虎咽。也许食物总是饥饿的时候吃起来更有味道,那种味道只能在乡间品味。
回响在重檐翘角的祠堂里
茅洞桥的甘氏宗祠、全氏宗祠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规模相对较大,意味着两姓出了很多人才。全氏在晚清湘军时代出了两员武将,一个是担任过陆海四镇总兵的全彰镐,钦敕花翎记名提督,诰授振威将军(从一品);一个是诰授云南楚雄协镇、敕授武显将军的全彰盛。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俩被历史的烟尘屏蔽了百余年,所幸近年经甘建华先生的努力发掘,相继进入了省市县志。
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祠堂里会举行戏曲表演。有些农村是祁剧,有些地方是花鼓戏,茅洞桥的特色是灯影戏(皮影戏),现在最有名的艺人是年过八旬的陈诗佾。灯影戏表演没有音响,全靠艺人的嗓音,加之不宜远观,近距离地感受那高亢的唱词在田野中回荡,会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特别效果。
现代人谈论的蓝图与梦想,在乡间简化为最通俗易懂的四个字——光宗耀祖。子孙后代有出息,祠堂里供奉的那些牌位都感觉有光彩,这也许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激励方式。
行走在茅洞桥,虽然看不到像桂林山水一般的画卷,亦没有像徽式建筑的黑瓦白墙,但这里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茅洞桥的乡愁如同一壶地道的农村米酒,又叫湖之酒,不像茅台、五粮液一般名声大噪,有的只是粗粝食材的醇厚,既有浓度又不醉人,香甜爽口,有乡愁在焉。
那些游子经过苦苦地追寻之后,也依然想回到这种日常。那些远去了的人情味,在这里一点点地苏醒。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云胡不归?”茅洞桥,向游子发出了心灵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