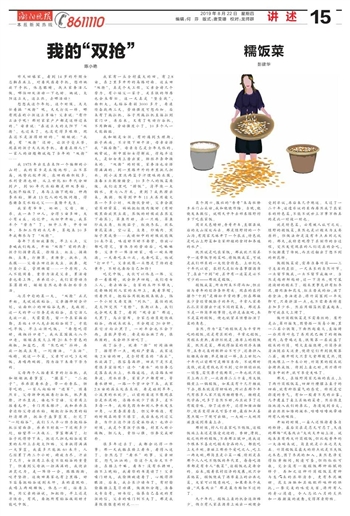某个周六,报社的“香哥”来马杜桥乡石门山采访,我和晓晓作陪。当晚,晓晓发来微信,说明天中午去祁东绿野村乡下吃农家饭。
周日天色晴好,香哥开车,直驱县城后的大山深处而去。那是绿野村的一个山沟,有周家兄妹开了一个农庄,特色就是吃山上野菜和自家种植的食材和养殖的水产。
既然说是吃农家饭,那我就只写其中一道带饭字的菜吧。将饭做成菜,可说是我们祁东的一大饮食特色。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农村凡是红白喜事摆酒席了,在出“十到”时,其中有一道菜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糯饭。
糯饭成菜,所由何来不得而知,但应该与昔年的经济条件有关。现在的农村摆个“十到”是稀松平常的事,但在那缺衣少食经常饿肚子的年代,平常人家要扎扎实实摆出十道不同的菜来,那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许是凑数吧,本不是菜的糯饭,便也就冒名顶替扮演了菜的角色。
当然,作为“菜”的糯饭是与平常所吃的糯饭,还是有区别的。平常之糯饭,用糯米煮熟,再拌烂就是。酒席上的糯饭菜,既然是菜,那就得按菜的程序来操作,五香之类的配料必不可少,还要拌入红糖或白糖。单是糖这一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那可是稀罕东西,不说那时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它归供销社统一销售,需凭票才能购买,一年也就只能买上两三斤。一次酒席二三十桌,用大铁锅煮上一锅糯饭,如果没有十几斤糖放下去,根本就没得甜味的,所以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人家只能用糖精替代。糖精是化学品,吃多了自然不好,而且放多了还有股苦味。除了这些外,还得加猪油翻炒,使其变得油光可鉴才好,最后加点姜葱点缀一下便可出锅,一大碗一大碗用递盘送到席桌上去。
那时候,村人们在家吃不饱饭,这糯饭端上来还是很受欢迎的。香甜,滑软,较之纯粹的糯饭,不再那么腻口,连我这个根本不喜欢吃糯米食品的人,都能吃上大半碗。若碰上那些个爱吃之人,吃上一两大碗,那简直是小菜一碟。特别是在那个人人吃不饱饭的年代里,每每吃酒席都是有专人“散菜”,这糯饭也是要分的。后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只分其他菜,糯饭便成了酒席桌上的公共之菜,大家可以随意地吃。如果要来个成语,“风卷残云”那是最为贴切不过的了。
九十年代,糯饭上桌的机会逐渐稀少,偶尔有人家在酒席上端出一碗便会受到非议,再后来几乎绝迹。又过了一二十年,这遭非议的东西居然成了农家乐的特色菜,不能不说世上万事万物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说是特色菜,必有被人认可之处。绿野的糯饭菜,虽然也是以糯米为主要原料,但做法却是没有半点共同之处的。那天,我特意观摩了其制作的全过程,突然发觉现在的人们还真的会吃,不仅颠覆了传统,而且还翻出了想不到的新花样。
做糯饭菜前,需要准备竹筒——三寸左右的直径、一尺来长的自然竹节,一头留节做底,一头不留节成敞口。当然是越新鲜越好,过一下清水,便可装进淘好的糯米了。糯米里事先拌有红枣泥、腊肉渣和花生、红豆磨成的粉,滴了些食油、香油进去,将竹筒塞到一半处即可,只要拌湿一点,也不需要再特意去加多少水。然后用锡箔纸蒙盖起来,即可放在火上烤了。
做竹筒糯饭菜是不需要灶的。屋外是山,翠竹摇曳,因势搭一简易小棚,置一二层小铁架,下面燃起柴火,直接烤一些用荷叶包了再用泥巴糊了的胡椒瘦肉、乌骨鸡之类,铁架第一层放盛了糯米的竹筒。明火直接烧烤,竹筒渗出清油随后又泛黄,便将它们升到铁架第二层,避开明火只靠火堂那股炙热,慢慢地煨上一个来小时,竹筒里的糯米就会烤熟成饭。待到上桌之时,用刀将竹筒当中剖开,就可享受美味了。
那天,在绿野周家兄妹的农庄,上了两竹筒糯饭菜,四瓣竹槽摆占桌子的四面,就有种很霸气的感觉。特别是它弥漫的香气,有如一股看不见的云雾,几乎覆盖了桌上其他的菜肴。然后很直接地浸入我们的鼻孔,再漫延到舌尖,诱出丝丝如缕的涎水,咕噜咕噜地带动所有人的喉结。
开始的时候,一桌人还保持着各自的矜持。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久违的那场“风卷残云”大戏又开始上演。说起来虽有两大竹筒糯饭,但比起昔年的一大海碗来说,简直就是小巫之见大巫。竹筒糯饭菜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失饭之本色,因了枣泥的加入,虽然色泽变得红黄相间,剔透可鉴,但仍粒粒可数,完全没有一般糯饭那种粘腻的样子。再加之这种竹筒糯饭菜有种与生 来的浓郁清香,更有枣泥嫩甜、花生油酥和其他配料味种的烘托,一餐完美的味觉大宴,将所有人的身心浸透,令人忘记八月的炎热和一路颠簸的疲惫,变得浑身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