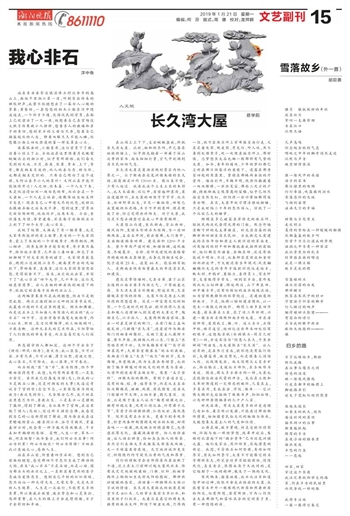人文赋
在山间上上下下,左右蜿蜒盘旋,终抵长久湾大屋。此时,融和的冬阳,早已落在斑驳的墙上,似乎抢先翻看一部藏于深山泛黄的家书。尚未细细打量,空气中就闻到清末民初的气息。
长久湾大屋是莲湖湾规划景区内的八景之一,位于衡南县近尾洲镇朱雅村长久组,距莲湖湾口约13000米。因往来不便,少有人逛过。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本村人,也久未谋面。记忆中,房前遍种莲荷,屋后漫植修竹,去大屋的田埂弯弯窄窄。此次来,水田野草丛生,不见一株枯荷,田埂已成宽敞的水泥路,车子可开到屋畔。便是便捷了些,但总觉得些许陌生。对于大屋,我还是不想去调整它在我心中原有模样。
大屋傍山而建,坐北朝南,背山面田,避风向阳,呈锁头形砖石木结构,为一进四厢两层,左右五开间,前出檐廊,大门居中,左右相连厢房回廊,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整个布局严谨对称、和谐协调,通风敞亮、冬暖夏凉。台阶、前坪及进院的甬路皆用精致的麻石条铺垫,石条之间相互咬合。院子通深25米,通宽46米,能容纳百把人,是衡南县现存体量最大的单进清末民初建筑。
建筑是带情绪的,尤其古居。匿于山区丘陵的江南古居多内敛之气,少有跋扈之感。长久湾大屋古朴雅致,舒适实用,无显摆极其宏伟的排场。大屋不仅是原主人欧怀德的思想遗存,还是一种富商文化的缩影,一个已逝时代的见证。欧怀德将人生追求和做人道理融入到筑建的大屋之中,勉励自己,以示后人。大屋两侧厢房前端,各出一对甚是讲究的侧门,石质门框上盖双坡瓦顶,门额镌“长久湾”,进屋前坪与厢房侧门间砌青砖围栏,反映了屋主人藏财不露、势不声张、低调做人的心态。门框上“长思皓月照千岭;久仰朱梅香百家”“长守荷田慕花开;久居茶室期客来”的石刻嵌联,及厢房门簪上“天长”“地久”的刻字,笔力雄健,书意饱满,既为大屋添香增墨,也折射了偏乡僻壤对传统文化的热衷与崇尚。从前坪到进房有五级台阶,寓意“五子登科”。四根木柱的雕饰,有别于普通古宅,没有刻福、禄、寿、禧等吉字,而是从左至右依次雕梅花、麒麟、凤凰、荷花图案。进房大门框镶竹节文饰,工细非奢,图凡意深。这些,应是缘于屋主人认为“梅有顽强之征,麒有祥瑞之象,凤有仁德之品,竹有君子之节”,寄意子孙顽强拼搏、仁德处世、高风亮节。院外没有名卉古木,更看不到奇观异景,但堂内各种构图精美的石刻木镂,却将品味一一收藏,既反映当时精湛雕艺,也渗透浓厚文化,蕴藏满满哲理,给人些许启迪,让人悟出禅意,恰如盏盏怡人的陈茶。虽然它们表面大多或皴裂或剥落或残缺,无一不裎露衰老痕迹,无言地诉说历史变迁,但隐隐约约可窥见往昔的气度和厚重。
同行的诗联学会老师将屋内屋后瞧了个透,还立在大门前研讨起大屋风水来。惟有我定定地凝视梁枋、门额、栏杆、柱础等构件上栩栩如生或阴或阳的图刻,那种熟识暖暖的感觉,涌动着一种缠绵而又难以言说的情愫。长久湾大屋距我的祖屋灵阁堂不足400米。儿时常去屋前古井打水,和湾里孩子们玩乐,也着实羡慕它的精美及独有的麻石大坪。即使下倾盆大雨,只待雨一住,就可在麻石坪上穿布鞋自由行走。尤其是看电影、观皮影、赏龙灯、听人戏,用不着到处借凳子,吹一吹便直接坐坪上。那时候,总梦想长大后也砌一栋那样有气势的大屋。如今,童年的嬉戏、少年的梦幻都已尘封在那日渐苍凉的梁檐下,遗落在那青苔四起的角落里,紧锁在那蛛网垂挂的厅堂内。墙后栏外,半晦半明,恍惚仍躲藏着一双双眼睛,一丝丝笑容。那些三尺方的户牖,精致玲珑尘埃厚覆的窗格,似乎已坦然接受自然变幻,但仍将一些旧景细解得棱角分明。其实,大屋早就习惯清静地酣睡,只是我时隔三十年的忽然闯入,惊扰了一个沉寂已久的睡梦。
踯躅在多已破裂杂草挤兑的麻石坪,轻抚风雨洗礼磨得光滑的门框,默念外墙清晰可辨的毛主席语录,时光沿沧桑的韵脚渐渐回溯至清末民初。当我执究大屋建成的具体年份和原主人欧怀德的家族史,问及陪同的村干部和围拢看我拍照的翁媪时,他们都茫然语塞、含糊其辞,还没有谁能说个明白。不过,从各种零星闲谈和童时奶奶讲述中,可大致还原当年境况:风度翩翩胸怀大志的青年才俊欧怀德远走他乡,贩木材、开钨矿、置银庄,善待员工,宵衣旰食,生意做得非常大。回到家乡后,意外发现此处山似神兽,绵延两边,山下布良田,田中镶古井,还有白练似的溪水缓缓流淌,如为官佩戴腰际的环带绕过,是建祖屋的好地方。于是,他精心绘制建房图纸,以一兜禾一块银元的地价,购得三亩多良田作地基,请来著名工匠,花了近三年时间,兴建一栋当时名闻衡阳南乡的大屋,并在房前种荷,屋周栽兰、梅、竹。竣工当日,正值中秋,皓月凌空,他回忆这些年来四处经商的艰辛,遂想起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并受其佳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启发,为大屋取名“长久湾”。让人诧异的,是在乔迁吉辰,欧怀德没有张灯结彩,大摆筵席,收受贺礼,而是携妻儿悄悄入住。抗战爆发后,他又深明大义变卖矿山,转让银庄,支援抗日部队,在当地传为美谈。随后,跟大多古居古祠一样,大屋也没能挡住政治风雷的冲击,先后在土改和文革时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几易其主,多易其用,变成农会、学校、粮库……它以博大胸怀先后接纳了琅琅书声、灿灿谷堆,以及种种原因栖身的几十户人家。
时光荏苒,有关大屋更多的详史逸闻已逝如水,着实难以发掘,只能透过那些构件图案,细细摸索民俗文化的脉络与传承,大致想象大屋主人的气度和性情。
山居是福,故乡萦魂。许是受欧怀德影响,怀揣与他一样的梦想,改革开放后,朱雅村北漂南下的“掏金青年”已为近尾洲镇之最。他们发家后,思归梓里,筑起漂亮的新宅。我想,不管麻石如何坚固,青砖如何厚实,黛瓦如何墨守,大屋不可能像它的名字那样长久,终究会任岁月轻轻剥蚀,慢慢风化,直至老去,惟图永存于天地间的,是它辐射于一地的精神,散发于一隅的文化。
寒风偶来,摇落斑痕,我亦从注目和漫想中回过神,依依不舍走出孤寂的大屋。我张望百米开外一栋栋现代新居和照看新居的阳光,似有所慰,若有所悟,可内心仍然丢失在那潮气和霉味混合的空阔屋子里,有一种隐隐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