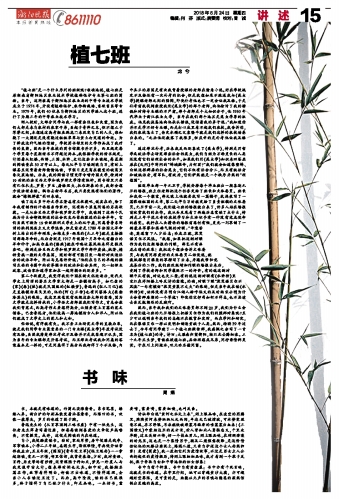“植七班”是一个什么序列的班级呢?准确地说,植七班是原湖南省衡阳地区农业技术学校植物保护专业第七班的简称。当年,这所隶属于衡阳地区农业局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74年,开设有植物保护、农作物栽培、畜牧畜医等专业。1979年,我们40位来自衡阳地区的同学编入这个班,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中等农业技术学习。
刚入校时,大部分同学与我一样有些沮丧和失望,因为我们大都是来自农村的农家子弟,虽起于青萍之末,但不想止于草莽之间。本想通过高考鲤鱼跳龙门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谁知绕了一大圈还是没有绕过祖祖辈辈与黄土打交道的命运。为了释放这种气馁的情绪,学校图书馆里的文学作品成了我疗伤的良药。然而当年农校的图书馆藏书并不多,而且规定每个学员每个星期借书不得超过两本。我根据学校的借书规定,计划着从红楼、西游、三国、水浒、史记这些古本读起,每星期的阅读量在50万字以上。每天从早自习读到晚自习,有时上课甚至还背着老师偷偷地读,节假日更是窝在寝室的被窝里昏天黑地读。后来,我的阅读习惯变得专嗜外国文学,特别对19世纪的法兰西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图书馆里只要有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书,我都会想方设法借来读。偶尔去新华书店,我只要发现有他们的著作,就会“慷慨解囊”买回来读。
读了这么多中外文学名著总有点收获吧,说实在的,除了令我有创作的冲动想当作家外,还有两个匪夷所思的另类收获。一是从法兰西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中,我读到了这两个民族为什么会鄙视渐进的社会改良而崇尚激进的社会革命。它们虽然可称为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的双子座,同属普鲁东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但是前者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树上结出的革命硕果,如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就是直接描写那场革命的。而后者则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播出的革命种子,如高尔基的《海燕》就在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特别是法兰西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中那种虔诚、执著、精神贵族一般的文学基因,随时都有可能引发一场针对改造社会的政治革命。所以马克思评价说:“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学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第二个收获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后,近代文学史上所谓的著名文学家大都是一些模仿高手,如巴金的《家》《春》《秋》就是民国版的《红楼梦》,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直接模仿果戈里的,他的《阿Q正传》也有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的痕迹。我这里丝毫没有诋毁这些大师的意思,因为文学就是这样传承的。小学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首先会教我们背范文,而高考作文要想得高分,必须要有上百篇的范文储备。巴金鲁迅者,他们技高一筹地模仿古人和洋人,所以他们就成了文学史上的范儿和大咖。
俗话说,有得就有失。我不务正业研究文学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所学专业最重要的一门专业课《昆虫学》年度考试没有及格。虽然我清楚那次考试不及格并不是我答题不认真,因为当年的专业课都是开卷考试,而且那次考试我和同桌的答案基本是一样的,可是同桌得了高分而我却得了个不及格,内中真正的原因是有次我背着授课的老师在偷看小说。好在学校规定不及格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但是我想如果不疏通我与《昆虫学》授课老师之间的隔阂,即使补考他也不一定会让我及格。于是补考前我找到教授我们《昆虫学》的那个老师,向他检讨了我的错误和对待专业课的不严肃。那个老师是个大知识分子,他1950年代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当年在我们那个地区是昆虫学界的权威。他见我诚恳地向他承认错误,便指着我的鼻子说:“我知道你并不是学不好专业课,而是打心底里看不起我们农校。我告诉你,我们农校怎么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是我们这样的农校培养出来的。”之后他还数落了我很多,但庆幸的是补考他让我及格了。
通过那次补考,后来我反而还喜欢了《昆虫学》,特别是用哲学或政治学去研究那些社会性昆虫,我们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还没有它们治理社会的水平。如果我们用《昆虫学》知识来回答屈原在《天问》中所问的“蜂蛾微命,力何固?”我们就会知道像蜜蜂、白蚁这样群居的社会昆虫,它们不仅有社会分工,而且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军队,有政府,它们俨然就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理想国”。
临近毕业那一年元旦节,学校安排每个毕业班出一期喜迎元旦的墙报,班主任老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班长和文体委员。班长和我住一个寝室,那天晚上他就要我写一篇稿子,我连夜写了一篇歌颂祖国的文章,第二天早自习时就交给了负责组稿的文体委员。元旦节前一天,我们植七班的墙报就出来了,许多人站在墙报前欣赏我们的杰作。我从头至尾看了两遍后总觉缺了点什么,特别是三年平淡无奇的农校学习和生活似乎有一种没有完成使命的感觉。我杵在人头攒动的墙报前思忖有倾,灵光一闪草创了一副兼具草莽和英雄气慨的对联:“辛遭苦逢,莫道窗下人少壮志;功成名就,敢笑诺贝尔不风流。”我想,如果把这副对联作为我们这期墙报的刊联,那岂不有画龙点睛的效果!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文体委员,与我有同样爱好的文体委员二话没说,就裁纸挥毫用漂亮的草楷写了出来,并邀我帮忙完成善后的工作。我们班改版增加刊联的墙报出来后,受到了学校老师和同学褒贬不一的评价。有的说这副对联平仄有误,对仗也欠工整;有的说这副对联有《水浒传》里宋江在浔阳楼上吟反诗的意境。的确,对联下联“敢笑诺贝尔不风流”一句有模仿“敢笑黄巢不丈夫”的痕迹,但是当年我在读《水浒传》时,始终没有弄明白江湖人称呼保义的及时雨宋公明为什么会崇拜唐朝的一个草寇?即使你宋押司如何不得志,也不应该去当反叛朝廷的反贼啊。
然而,当年我和我们的文体委员都不到20岁,我们为什么会在我们植七班的元旦墙报上把诺贝尔作为我们的膜拜对象呢?至少可以说明当年我们的志趣不在做官和发财,而在学问和研究,而在像诺贝尔一样以发明和创造贡献于人类。然而,转瞬39年过去了,今年有同学建了一个植七班微信群,我感慨之余写了一首名为《植七班》的诗。诗曰:大雁南归望衡阳,湘江北去腾细浪。三十九年庄生梦,曾读农校植七班。共话理想成兄弟,同抒豪情拜炎黄。子在川上问逝水,叹无功名慰同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