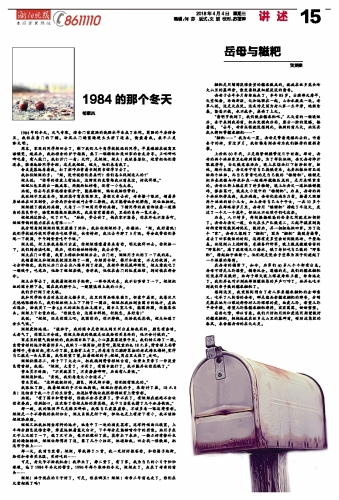糍粑是用绵绵淡雅金黄的糯米做成的,就放在故乡荒头岭大山里的墓碑旁,散发着轻盈细腻淡淡的清香。
岳母于去年冬月匆匆地走了,享年85岁。出殡那天清早,天空低垂,冻雨淅沥,天和地联在一起,山和水凝成一块。老辈人说,这是天在哭。这或许是因为老人家一生辛劳,饱经沧桑,坚忍不拔,永不放弃,感动了上天。
“清明节快到了,我们做些糯米粑吧。”几天前的一顿晚饭后,妻子来到我面前,把头发摸向后面,露出一脸的遗憾,接着说,“去年,母亲压根就没想到死,临别的前几天,她还要我从衡阳带糯米糍粑……”
“糍粑……”我为之一震,岳母是带着遗憾而去的。听着妻子的话,穿过岁月,我仿佛看到岳母为我们操劳的瘦弱身影。
上世纪60年代,正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时期。那时,岳母的两个妹妹家里也特别困苦。为了帮扶她俩,岳父岳母睁开眼就劳作,白天做完农活后,晚上在煤油灯下纺纱织布,织袜,缝补衣服。岳父母宁肯自己挨饿受冻,也要把粮油布匹送给两个妹妹,而自己常常吃的是自己做的“糠饼粑”。糠饼是把谷壳米糠与碎米和在一起碾碎搅糊压成的,是用来喂家畜的。岳母从街上粮店买了许多糠饼,晚上与岳父一道把糠饼搅碎,掺些菜叶,做成大小适中的“糠饼粑”。后来,岳母的两个妹妹积劳成疾,先后病逝。岳母化悲痛为力量,接着又照顾两个妹妹的幼小儿女,加上岳母自己七个子女,一共10多个孩子。在那艰苦岁月里,岳母用“糠饼粑”撑起了半边天,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荒年。但她从不让孩子们吃这些。
后来,人口增多,那间摇摇欲坠的安身之所就更加拥挤了。岳母与岳父一道,白天在生产队做完工,又起早摸黑到高岭祠堂附近做泥砖泥瓦,做好后,再一担担地挑回家。为了这个“家”,岳母又想到了“糍粑”,因为“糍粑”能随身携带,省去了回家做饭的时间,这样有更多空余时间做泥砖、平整地基。她便到山上挖树根,采摘各种野草,晚上做成酸酸苦苦的“野菜粑”。渴了就近喝几口塘水,饿了匆忙吃自己做的“野菜粑”,撸起袖子继续干。他们硬是凭赤手空拳为孩子们建起了一个温馨的港湾。
在岳母的福荫下,如今,后辈们40多人个个都有出息。岳母可谓是儿孙满堂,福寿双全。遗憾的是,我们的糯米糍粑还没来得及做好,她却于那天晚上深夜寿终正寝,匆匆地走了。我们再也听不到她那温暖轻柔的声声叮咛了,她再也吃不到我们亲手做的糯米糍粑了。
想到这里,我突然间明白了老人家要糯米糍粑的全部意义:吃尽了人间苦的岳母,哪是想品尝糯米糍粑的醇香,分明是藏在她内心深处那份对儿孙深深的爱,她爱儿孙,希望儿孙平安幸福,希望儿孙像糯米糍粑那样,团团圆圆,甜甜蜜蜜。
悲伤之情,难以言表。我们只好把用泪和爱连同期望做好的糯米糍粑,轻轻地放在故乡大山里的墓碑前,借助这柔软的春风,来告慰岳母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