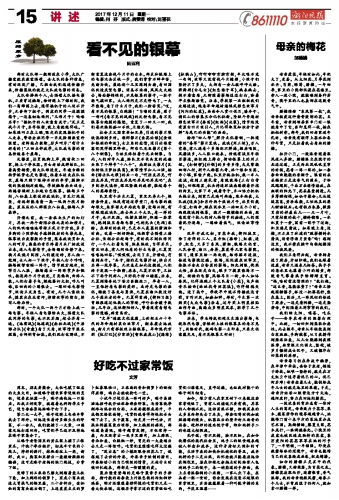那时大队部一般附设在小学,大队广播室就在教室隔壁。全大队的各种信息,有时还没广播,已经由我们迅速传播开来,传播最快的就是大队放电影的消息。
大队安排两个人,去隔壁大队接电影机,正要穿过操场。恰好遇上下课时间,我们一窝蜂围上去,逼得接机子的人迈不开步,无奈卸下担子。调皮的同学一边摸摸箱子,一边急切地询问:“几部片子?吗咯名字?”接机子的人故意卖关子:“反正是战斗片子,名字保密,晚上看就晓得哒。”如果碰巧正在上课,眼尖的发现接机子的人走来,带动全班同学一齐反脸朝教室外张望。老师敲击教鞭,厉声呵斥:“有什么好看的!”三四点钟放学,大队放电影的消息传遍各个屋场。
天擦黑,社员洗脚上岸,提前收工回家,换上干净衣服。男女老幼成群结队,扛着高凳矮凳,朝大队部进发。年逾古稀的柏爹栋爹也是电影迷,拄着木杖夹在队伍里,屋场只剩下眼神不好的争爹,腿脚不便的张娭母也刘娭母也。学校操场南头戏台,两株苦楝树上扯起白色银幕。操场正中间,八仙桌上架设好放映机,百瓦灯泡通亮,老远都能看清一高一低两个胶片轮盘。黑压压的人群围坐八仙桌,操场人声鼎沸。
开演之前,放一套农业生产的幻灯片,再放一两个新闻公报之类的加演片。人们叽叽喳喳地等待正式片子开映,多手多脚的小孩举起手遮挡投射的电影光束,银幕映出皮影般的手型,惹来放映员和大人的呵斥。熟悉的音乐伴着片头厂标放送出来,进入电影情节,全场顿时安静下来。换片或烧片间隙,人们缓过神,男人抽一兜烟,女人奶一下孩子,年轻人打个呼哨,操场短暂喧闹一阵子。情节跌宕起伏,故事引人入胜,操场爆出一阵阵掌声和慨叹。接连两个片子放完,月亮偏西,曲终人散。人们打着手电,燃起葵杆火把,呼儿叫娘,沿四向的小路散去。一路回味电影情节,议论正反角色。有时,几个人意犹未尽,摸黑坐在禾堂坪,推演故事的留白,续写人物后传。
那时,一个大队一两个月才轮上放一场电影。年轻人看电影劲头大,隔壁大队放同样的电影,也不厌其烦,赶去再看一遍。《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奇袭》看了又看,故事情节滚瓜烂熟,台词倒背如流。我们玩打仗游戏,不断重复这些战斗片子的台本。郊区和铁路上的电影比县区快一步,我们常常不辞辛苦,先睹为快。最远赶十几里路到头塘,看田园化改造庆贺电影。消息不准确,风风火火跑去,场面静悄悄的,不见银幕的影子,一肚子怨气摸回家。大人询问是不是停电了,一大早散场,看了什么片子,我们一脸苦笑:“哎,看不见的银幕,白跑腿!”自嘲的灵感,源于一部叫《看不见的战线》的反特电影。看不见银幕白跑腿的尴尬,重复了一回又一回,我们每次依然痴心不改,无怨无悔。
社会主义国家亲如兄弟,引进的影片很快流转到乡村。朝鲜影片《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女主角的悲情,逗引姑娘堂客们哭得稀里哗啦。阿尔巴尼亚影片《第十八个铜像》,自始至终抬着个光头铜像。自此,人们对号入座,给队里不长头发的疤癞头取了个绰号“十八个”。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插曲《游击队之歌》的头一句,“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在乡间持久流传,深沉坚毅的旋律,激起每个人的英雄豪情。
队里有个后生元夏,家里兄弟九个,经济条件差。他没有进过学堂门,看电影的瘾却很大,朱家堰火车站放电影,逢场必到,有时跟随放映队,连去两三个大队,看一样的片子,也不厌烦。他捞鱼摸虾,积赚一些零钱,跑到城里看场电影,吃碗光头(免码)米粉。在那时的农村,已是令人羡慕的潇洒和时尚。仗着一副好脚板,他经常去隔壁三塘公社、长湖公社赶场子,有时找不到伙伴同行,一个人打着电筒,独来独往,自得其乐。有次回来,有人问他看的什么电影,元夏笑嘻嘻地回答:“嘿嘿嘿,去迟了点,开演哒,冇看到头子。”头子,指的是电影开始,推出片名那一段序幕。几次总是如此这般说,人们终于发现一个秘密:原来,元夏不识字,又拉不下面子问别人,只好找个借口搪塞。后来,元夏到港务处下苦力当搬运工,单身一人,一直保持看电影的爱好。或许是电影的教化,铸就了善良与勇敢,元夏在湘江救过好几个落水者的命。元夏得重病,《衡阳日报》曾经报道过他救人的事迹,呼吁社会援手救助。几年后,这位衡阳好人,带着没有看够电影的遗憾,病重离世。
“文革”造就文化荒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题材黑白故事片,翻来覆去地放映,新片只有样板戏占据银幕。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杜鹃山》,啊啊咿咿京腔京韵,半天唱不完一句词,故事又没有战斗片精彩,小孩子们坚持不了多久,大都看一会儿就呼呼大睡。歌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跳来跳去,搞不清意思,无聊围着影场追追打打,盼着早点散场睡觉。后来,学校第一次组织我们走路进城,观看革命题材遮幅式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画面令人赏心悦目,潘冬子、胡汉山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阶级斗争题材彩色故事片《春苗》《红雨》《决裂》,情节远没有黑白旧片吸引人,只记得取笑知识分子讲解“马尾巴的功能”的画面。
粉碎“四人帮”,解开文化禁锢,一批遭禁的“毒草”影片复映。放映《刘三姐》,万人空巷,有人连看十多场还不解渴,经典唱段,风靡城乡,人人张口就来。传说有城里年轻男影迷,抓狂跑上舞台,拥吻银幕上的刘三姐。《打铜锣》《补锅》的乡音乡情,久久萦绕四邻八村,剧中人物蔡九哥、林十娘和兰英、李小聪,家喻户晓。队里开拖拉机,载一车人进城,赶到三建礼堂,看晚晚场《三打白骨精》。回程路黑,机头掉进环城南路横着开挖的沟里。大家下车,喊着号子,齐心协力把机头拖出来,到家已是鸡叫两遍。寒冬雨夜,大队放《追鱼》和另外两个热映片子,社员们戴斗笠、打雨伞,踩在泥水里一站四五个小时。雨线投映到银幕,烧片一般模糊的画面,丝毫没有干扰人们对人物情节的痴迷。人们探着泥泞退场,一路哈着热气,议论故事情节。
改革开放之初,百花齐放,衡阳城里,除了老牌的工人、东方红(雁峰)、红旗、进步、红色,又多了东风、潇湘、铁路文化宫、人民会堂、湘江、岳屏、翼星等几家电影院。假日,逼家里给一两块钱,结伴搭车进城,钻进电影院过瘾。散场,还沉浸在故事里,依依不舍走出昏黑的影场。阳光刺眼,恍然大悟,原来还是白天,跟乡下摸黑散场不一样。新拍的电影,风格耳目一新,令人如沐春风。记得连跑三个大队看《小花》,电声轻音乐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听得销魂失魄。进了高中,学校早中晚不停播放这首歌,百听不厌,如痴如醉。那时,平生第一次购买《大众电影》杂志,过年买上明星招贴画作年画,熟稔众多明星风采,剽学了几个电影术语。
后来,学业将我们硬生生逼出影场,电视取代电影,苦楝树上挂的银幕真的看不见了。网络时代,数码电影一点即来,只要文化意蕴充足,看不见银幕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