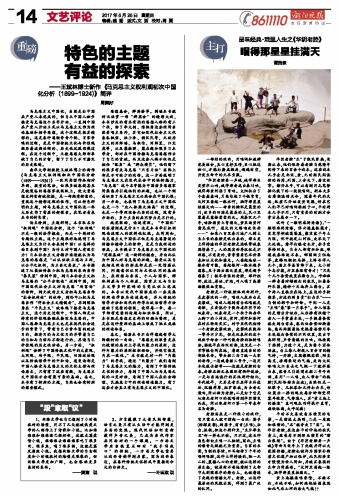唱得那星星挂满天
谭浩泉
一部好的戏曲,用唱词和旋律完美结合,真心直抒真情,匠心抵达初心,方能打磨成经典,超越时空,开发生命中的无尽宝藏。
“华阴老腔要一声喊,喊得那巨灵劈华山呐,喊得那老龙出秦川呐,喊得那黄河拐了弯呐。太阳托出了个金盘盘呐,月亮勾起了个银弯弯,天河里舀起一瓢水啊,洒得那星星挂满天呐……母亲的胸怀是最宽的川,故乡的田园是最美的土,民心里装着是蓝格莹莹的天。周秦汉几千年,咱脸朝黄土背朝天,梦里面黄河清见底啊,通天的大路咱走长安……”如果八百里秦川地广人稀土生土长的秦腔是吼出来的,那么更土得掉渣的华阴老腔是连吼带喊表现情感了。人的现实世界往往是不理想,不完美的,常常需要艺术世界来加以点化和满足。人舀起地球一瓢水有可能,舀起银河一瓢水超乎想象。至于洒出满天星星,那是超乎想象了!极尽夸张的老腔,那种粗野、放达、原始、旷远,叫人喝了高粱酒般热血贲张。
老腔是一种板腔体戏曲剧种,是皮影戏的一种,唱戏人在后台是皮影戏,唱戏人跑到前台吼唱就是老腔,主要流行于陕西省华阴市的双泉村。双泉村是一个位于西岳华山脚下的小村庄,黄河、渭河和洛河在村庄附近交汇。村子里代代相传一个老腔皮影戏班,皮影戏在陕西一带并不少见,但是双泉村的这个戏班子却会一种叫做老腔的独特唱法。据说早在西汉时期,这里是一个军事粮仓所在地,漕运直通当时的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大家的动作,一边喊着船工号子,一边用木块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老腔名称之来源还有两种说法,一是与当地流行的其他剧种相比,年代较早,尤其是音乐显得古朴悲壮、沉稳浑厚、粗犷豪放,为古老之遗响,所以称为老腔;二是由于它是从湖北老河口的说唱传到华阴演变而成,所以取老河口第一个字来命名为老腔。
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签手(指挥皮影)、副签手、前首(主唱)、后台、板胡。但这个剧种里,“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自家的木凳,自制的琴弦,口耳相传了千年的唱词唱腔,这种土得掉渣的、独一无二的、震撼人心的老腔,就以这样的原生态,被原封不动地请到了大都市大剧院豪华的舞台上,也被请进了央视的演播大厅。老腔,以这种最原始的风貌出现,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
华阴老腔“生”于张氏家族,长期以来,他们保存着老腔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戏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唐宋故事。翻开本子,可以看到用毛笔竖排记载下的一段段唱词。剧本大多由清朝流传至今,随着年代的久远,纸质已开始发黄变脆,好在艺人们早已对唱词铭刻于心,平时剧本几乎不用,只有重要的时刻才会拿出来展示一下。
试听《一颗明珠卧沧海》:“一颗明珠卧沧海,浮云遮盖栋梁才,灵芝草倒被蒿蓬盖,聚宝盆千年土内埋。怀中抱定山河柱,走尽天下无处栽。清早打粮仓未开,赤手空拳转回来,自古人都有兴和败,难道我秦琼运不来。哪国烟尘犯地界,皮褥双锏把马排,上阵杀得人几个,唐主爷圣旨降下来。大小封个乌沙戴,方显秦琼有奇才!”只见十几个条凳放置在舞台上。呼啦啦一群身着对襟短打的农民,扛着各种乐器,精神十足地奔上舞台。其中两人直接坐在地上,左边的手持胡琴,右边的则负责“打击乐”——自制的梆子和钟铃。中间一人是“主唱”兼“第一月琴手”。令人惊喜的是演出开始后,从后排有位精干老人一手拿着木块,一手提着条凳就走到台前来,忽而让条凳四脚着地,忽而两腿着地变换着姿势用枣木块敲打条凳的不同位置,发出节奏鲜明、声音清脆的巨响。他抡圆了胳膊,力道十足,是为整个团体助威。台上每人都投入百分百的精气神,一开腔,立现慷慨悲歌、刚直高亢、磅礴豪迈的气魄,关西大汉咏唱大江东去之气慨一下就抖落出来,落音又引进渭水船工号子曲调,采用“一人唱,众人帮合”的拖腔(民间俗称为拉波),虽然仅是一位歌手、几把琴和几件打击乐,却让最后一排的观众每分钟都觉得震耳欲聋、气势逼人。其“黄土地上的摇滚”直叫观众听得热汗直冒,痛快淋漓,大呼过瘾!
平时不大喜欢看名演员的电影,一是演技太高明,二是一看就知谁演的,“名”就夺走了“实”。而华阴老腔,在这些平时种地的农民身上,丝毫看不到职业演员的“演出痕迹”。由于《华阴老腔要一声喊》等曲目近年上了央视并得以大范围传播,老腔也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此民间珍宝才慢慢为世人所知,并被其表现的生命力所感动。“天河里舀起一瓢水,洒得那星星挂满天。”
黄土地摇滚唱豪情,不拍不打,不喊不吼,如何痛快淋漓表现如此气吞山河的浩大气魄!?